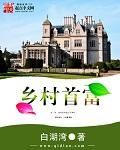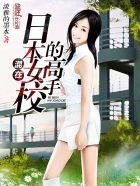笔趣阁>我是如何当神豪的147网 >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章 菲菲(第1页)
第一千五百五十三章 菲菲(第1页)
万菲菲住在别墅一楼的深处。井高感觉到她柔嫩的手心有些热,传来的力道有点莽,显示着她激荡、娇羞的情绪。
过一楼入门客厅,转入通往左侧的走廊。
宽敞的走廊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几幅当代水墨大家的写意。。。
清晨的阳光穿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光影条纹。井高坐在书桌前,手指轻敲键盘,一封正式辞职信已草拟完毕,标题是《关于辞去井氏集团CEO职务的申请》。他没有立刻发送,而是将文档最小化,打开邮箱里收藏的一封旧邮件??那是三年前董事会否决“萤火计划”时,他第一次在内部系统提交的社会价值投资提案,批注栏赫然写着:“理想主义泛滥,财务回报不可控”。
如今那封被退回的提案,已被员工自发打印张贴在集团创新中心走廊最显眼的位置,下方贴满了便利贴:“现在我们叫它‘起点’。”“谢谢您没放弃。”“我女儿上周去了帐篷图书馆。”
他关掉邮箱,起身走到阳台。城市刚刚苏醒,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如细碎银线,而楼下巷口,一位老人正弯腰整理修鞋摊的工具箱,动作缓慢却坚定。这画面让他想起敦煌日出前的寂静,那种万物尚未喧哗、唯有存在本身在低语的时刻。
手机震动,清霜发来一张照片:第156窟南壁仕女图左侧经光谱扫描后显现出半幅模糊面容,眉形与主像对称,耳坠符号方向相反,确为双生姐妹无疑。配文只有两个字:【醒了。】
他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把名字藏进画中褶皱??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怕某一天,有人会彻底忘记她们曾活过、爱过、悲伤过。就像林薇产后抑郁最严重那晚,在医院走廊喃喃自语:“我觉得自己像块用过的抹布。”可就在昨天,她发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女儿踮脚给她系围巾,caption写着:“我的小太阳学会照亮妈妈了。”
他回了个拥抱表情,随即点开语音通话。响三声后接通,背景有风声和鸟鸣。
“你在哪儿?”他问。
“研究院后山。”清霜声音清亮,“刚做完晨检。你说得对,慢下来才能看见更多东西。今天我们发现第220窟顶部有一圈极淡的金粉痕迹,起初以为是脱落,后来才发现是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正好对应洞窟朝向。”
“唐代人观测天文?”
“更可能是象征意义。”她说,“引导亡魂升天的路标。你知道吗?很多供养人捐资绘壁画,并非为自己祈福,而是替已逝亲人完成未竟心愿。”
他闭上眼,脑海浮现李曼母亲扫街的身影。那个总在凌晨四点出现的女人,一边挥动扫帚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歌声飘散在空荡街道上,无人倾听,却真实存在着。而现在,“触觉美术馆”项目已被纳入国家残障儿童美育试点,教育部派人考察那天,李曼站在讲台上说:“艺术不该只用眼睛看,它该被触摸、被听见、被呼吸。”
“我在想,”他轻声说,“如果我们把‘流动美育站’做成移动车厢呢?改装几节退役火车车厢,配上太阳能板、投影仪、盲文画册、便携式陶艺窑……沿着铁路线走,停靠在县城、乡镇、牧区学校门口。”
“你会破产的。”她笑。
“我已经破过了。”他坦然,“真正的财富不是账户余额,是你能让多少人感到‘被看见’。当年我砸钱办慈善晚宴,请明星站台,媒体头条写‘神豪井高豪掷千万’,可第二天新闻就被股市暴跌盖了。但去年冬天,我们在青海一个雪灾封锁的村子里搭起帐篷图书馆,有个孩子读完《海蒂》后画了幅画寄给我??雪山顶上有扇窗户,透出暖黄灯光。他说那是‘希望的样子’。”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她说:“如果你真要辞职,我想带你看个地方。”
三天后,他坐上了飞往兰州的航班。清霜没说目的地,只让他带上防护服和笔记本。落地后换乘越野车,一路向西,穿越戈壁滩与干涸河床,最终停在一处几乎被风沙掩埋的废弃石窟群外。这里不属于莫高窟体系,鲜有人知,当地人称其为“哑窟”??因历代战乱频仍,许多画工被迫中断创作仓皇逃离,留下大量未完成壁画。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坦因曾试图进入,但被沙暴阻断。”清霜边走边解释,“我们最近通过卫星遥感发现地下有异常热源,推测可能存在未登记密室。”
他们戴上头灯,钻入一条狭窄通道。空气潮湿阴冷,墙壁上残留着未上色的线描稿:一队商旅牵驼穿行沙漠,孩童手捧莲花回头张望,女子倚门凝视远方……每一笔都带着急促的颤抖,仿佛画家知道时间不多。
在最深处一间小室,清霜停下脚步。墙上一幅残破壁画中央,站着一名执笔女子,面容模糊,衣袖沾满颜料。她身前摆放着调色盘,上面用极细线条勾出五个符号,竟与“她创空间”LOGO中的元素惊人相似。
“这不是唐代作品。”清霜低声,“碳十四检测显示,这间密室封闭于1942年。这位女画师,很可能是抗战时期流亡至此的艺术家。”
井高蹲下身,用手电筒仔细照看调色盘边缘。在那里,他发现了三个微小汉字:**林昭月**。
心猛地一沉。
“这个名字……”他声音发紧。
“你母亲。”清霜点头,“我们在整理一批民国美术档案时偶然查到。林昭月,北平艺专首届女生,擅长工笔重彩。1937年北平沦陷后失踪,官方记录为‘死于战火’。但她其实一路南下,参与过长沙临时画院、昆明壁画运动,最后出现在敦煌一带。”
他伸手抚过那三个字,指尖微微发抖。母亲在他五岁那年病逝,记忆早已模糊,只剩一张泛黄照片:年轻女子抱着男孩站在画架前,笑容温婉。父亲从不谈她,家族相册里她的影像全被剪除。他曾以为她只是个普通家庭主妇,没想到她竟是那个年代少数敢于提笔抗争的女性艺术家。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也许他们也不知道。”清霜说,“或者,选择了遗忘。但你看??”她指向女子手中画笔,“她没放下。哪怕孤身一人,身处绝境,仍在记录这个时代。”
泪水无声滑落。他终于明白为何自己会对“看不见的女人”如此执着。原来早在血脉深处,就埋着一把火种。
他们在密室外扎营两夜,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紧急保护性勘察。井高全程参与,亲手清理浮尘,记录每一寸剥落痕迹。第三天清晨,他在女子画像裙裾背面发现一行小字,墨迹虽淡却不容忽视:
>**愿后来者,不止于观赏美,更要成为美的见证者。**
他跪坐在地,久久不能言语。
返回城市的航班上,他写下一段话发给“清源”全体成员:
【我们常问:一个人能改变什么?
今天我知道了答案??
你可以让一段被抹去的历史重新呼吸,
可以让一个被忽略的名字再次被人念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