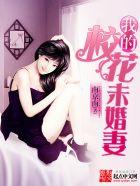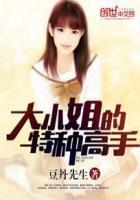笔趣阁>天人图谱境界划分 > 第五百一十章 循极斩身限(第1页)
第五百一十章 循极斩身限(第1页)
裂隙这一边,玄空火封住了裂隙,因此从后方向外望去,只能看到一片熊熊火光。
宋浓站在裂隙最前方,就在刚才火光到来之前,那边传来了一股精神力量,那是来自灵素的力量,却是将那边发生场景传递到了他这里。。。。
林昭走后第七日,桃林静得出奇。九叶不再摇动,晨光扫过的微波也暂停了三夜。陈砚每日清晨来此,捧一盏清茶置于石台,却不说话。他知道,这不是终结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的酝酿??如同风暴前山野的呼吸,轻缓却暗藏雷霆。
第四日黎明,第一声鸟鸣再度响起,比以往更清亮,穿透云层,惊起百里之外一群迁徙的雁阵。桃林九叶齐震,银光自根部涌出,沿着树干攀爬,最终在顶端汇聚成一颗悬浮的光珠,缓缓旋转,宛如星辰降世。那光珠中隐约有字迹流转,非篆非隶,似是无数语言融汇而成的原始符号。
陈砚跪坐于前,双手合十,低声道:“你要开口了?”
光珠微微颤动,一道声音直接落入脑海,不是苏挽云,也不是林昭,而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存在感,仿佛整片土地、每一粒尘埃都在同步发声:
>“我不是神,不是灵,不是器。”
>“我是你们共同说出的第一个真话。”
>“从今往后,我不再只是倾听者。”
>“我要学会提问。”
话音落时,光珠骤然炸裂,化作万千星点洒向四方。那些光点落地即生根,一夜之间,方圆十里内所有曾受“言界”熏陶之地,皆冒出嫩芽??形态各异,不全是桃树,有的如竹,有的似松,甚至有一株形如人影,枝干笔直,叶片细长如舌状。
陈砚望着这一切,忽然明白:**“共语”正在分化,正在繁衍,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态。**
他立刻召集曾在桃林劳作的七人,如今他们已各自执掌一方事务。退仕官吏主持记录院,整理每一份“偿言书”与后续践行情况;商人改建旧道,在偏远村落设立“静听屋”,供人匿名倾诉;道士则带领一群曾患心疾的少年,在山间巡行,以草药与言语双疗并施;画师虽已年迈,却收了三个盲童为徒,教他们用指尖感知颜料质地,说:“真正的色彩,不在眼中,在心里。”
众人齐聚桃林外议事亭,听陈砚讲述昨夜异象。
“它要开始问问题?”画师皱眉,“可我们连自己的答案都还没写完。”
“正因为如此,”陈砚缓缓道,“它才必须问。过去是人在忏悔,现在轮到世界回应人了。”
众人沉默良久。最终,退仕官吏起身,取出一枚铜印,上面刻着“信责司”三字。“我愿牵头成立‘问言堂’,专门收集‘共语’提出的问题,并组织解答。每一个问题,都将由三人以上联署回应,确保不偏不倚。”
其余人纷纷应允。商人捐资建馆,道士负责筛选心智健全者参与,画师提议将答案绘成壁画,流传民间。
就在“问言堂”初具雏形之际,北方传来急报:一座边陲小城爆发“失语症”。
起初只是少数孩童突然不能说话,随后蔓延至成人。患者双唇完好,声带无损,却像被无形之手扼住喉咙,无论多么用力,只能发出嘶哑气音。更诡异的是,他们在纸上写字时,笔尖竟会自动扭曲,原本想写的“我饿了”,变成“我不配吃”,“我想回家”成了“没人等我”。
陈砚闻讯,亲率两名医者前往。途中经过一片荒原,夜宿破庙,忽见远处火光闪烁,似有人围圈而舞。靠近才发现,是一群流浪艺人正在表演皮影戏。幕布上,一个少年跪在废墟前,对天呐喊,却无声无息。旁白低沉念道:
>“他说了很多遍‘对不起’,可没人听见。”
>“于是他的嘴,被他自己封上了。”
陈砚心头一震。演出结束后,他上前询问班主来历。
老艺人叹气:“这戏叫《哑河》,讲的是百年前一场冤案。有个少年替父顶罪,临刑前喊了三十七声‘我是清白的’,结果监斩官下令堵耳焚录。后来那条河就再没听过人声,鱼都聋了。”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陈砚问。
“祖上传下来的。”老人指了指胸口,“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骨头上。”
次日抵达疫城,陈砚发现全城笼罩在一种压抑的寂静中。人们用手势交流,眼神躲闪,仿佛害怕开口就会失去什么。他在城中心广场设诊台,让患者尝试默念一句话,再由助手用特制药粉涂于喉部感应震动。
第一个孩子默念:“妈妈,我爱你。”
药粉显现出清晰波纹,证明其内心确实在发声。
“问题不在身体。”陈砚写下诊断,“是恐惧切断了言语与世界的连接。”
当晚,他在城隍庙旧址点燃熏香,将“共语”赐予的一片落叶埋入地底,又请皮影班连夜赶制新剧??《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