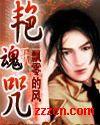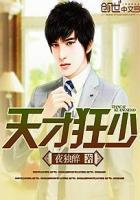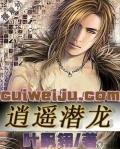笔趣阁>少女前线141指挥官全文免费阅读 > 第1308章 互联网大厂(第2页)
第1308章 互联网大厂(第2页)
她说完后,便没再说话,只是盯着地面上的油污发呆,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缝里的污垢。
伊芙琳当时没有接话。她只是垂着眼,手里攥着的抹布被捏得变了形,布料里的水分似乎都要被挤出来。
她能感觉到心里头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浸了水的棉絮,又沉又闷,堵得她喉咙发紧,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她知道克罗琦说的是实话,也知道这样的“实话”在这车间里有多不值钱——她们都清楚,那道“按规定来”的墙,不是某个人砌的,是无数次尝试后的沉默,是无数次冰冷的回应,一点点垒起来的,厚得连光都透不进来。
火神重工的车间里,这种透着邪性的荒唐事,天天都在上演。铁皮房顶下,机器轰隆轰隆转个不停,那些没道理的规矩、没人敢说的妥协,也跟着齿轮转,一遍又一遍——跟戏台子上的老戏似的,没剧本,却总也演不完。台上的人动作僵得像木偶,台下的人看着眼熟的桥段,没人觉得怪,更没人敢说句“不对”。车间里的灯是冷白色的,照在锈得掉渣的机床上,也照在工人脸上,连影子都硬邦邦的,好像连光都被这“常态”冻住了,没了活气。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大家早都麻木了。
上班铃还有两分钟才响,工位前已经杵满了人,手要么插在磨出毛边的工装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旧工牌;要么搭在机床边缘,指尖无意识蹭着积灰的锈迹。机器还没预热,齿轮静得能听见荧光灯的“嗡鸣”,可没人敢找个角落歇着,连靠一下机床都要绷紧肩膀——这种站着的“仪式”,早不是规定,却比规定更牢地捆着所有人。
没人问过“为什么要提前站着”,也没人试过晚来半分钟。就像没人会问“为什么要等铃响才开机器”一样,这种毫无意义的等待,成了工作本身的一部分。他们的目光空茫茫落在前方,有的盯着机床的铭牌,有的盯着地面的油渍,连眨眼都慢半拍,仿佛眼皮上坠着铅。身体是僵的,肩膀垮着却不敢放松,手插在口袋里也没个舒展的姿势,像被无形的线提着的木偶——不是没力气动,是动了也没用,久而久之,连“想动”的念头都磨没了。
到了开工时间,搬零件的动作更透着荒诞。明明从货架到机床,抄近路能少走两步,可每个人都绕着墙角的黄线走,鞋底磨破的地方硌着地面的小石子,每走一步都有细微的刺痛,却没人吭声。有人鞋底的胶都开了,露出里面的棉线,走路时拖着点趔趄,也只是把腰挺得更直些,生怕被看出“不合规矩”。零件压在手腕上,青筋冒出来,指节攥得发白,可路线半分都不敢偏——这种没效率的流程,没人质疑“为什么不能改”,仿佛绕路本身就是“工作该有的样子”,浪费的时间不是时间,是“守规矩”的证明。
手冻得通红也没人提换手套。车间的窗户漏风,冬天的冷空气裹着机油味往袖口钻,指尖冻得发僵,捏零件时都要先搓两下,可没人敢去找组长说“要副新手套”。不是没手套,仓库里堆着好几箱,只是“没人提”成了默认的规矩——提了就是“多事”,提了就是“嫌活累”,久而久之,冻红的手、磨破的鞋,都成了工装上该有的“痕迹”,像机床的锈迹一样,没人在意,也没人想擦。
看见不对劲的地方,眼皮一耷拉就挪开目光,比谁都快。机床的螺丝松了,零件歪在卡槽里,明明伸手拧半圈就能归位,可路过的人只会脚步顿一下,指尖动了动又缩回去,眼皮往下一垂,仿佛那处别扭本就该长在那儿。有人操作时姿势不对,明明多拧半圈就能省劲,旁边的人也只是看着,连提醒的话都懒得说——不是看不见,是“多管闲事”的代价比“看着出错”更大。他们宁愿多花十分钟调整自己的姿势,让腰更酸些,也不敢提“该拧拧螺丝”;宁愿忍着零件卡壳的不适,多试几次,也不敢打破“少说话”的默契。
这种麻木像车间地上积的厚油,裹着所有人的手脚。干啥都慢半拍,搬零件慢,拧螺丝慢,连抬头看钟都慢,动作机械得像生锈的齿轮,转一下都要费老大劲。他们的神情呆滞,脸上没什么表情,笑是挤不出来的,皱眉也只是一瞬,仿佛连情绪都被油裹住了,散不开也透不出来。车间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里面有机床的锈味、机油的腥味、荧光灯的嗡鸣,没有别的;他们的存在,就是围着机床转,拧螺丝、搬零件、等下班,重复着没生气的动作,像被车间吞噬的影子,连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种麻木早不是“习惯”,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提前站着、绕路搬零件、视而不见,这些动作不用想就会做,像齿轮转起来就停不下。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噩梦”可言,因为连“醒着”的感觉都没了——每天走进车间,就像把自己放进油里,裹着麻木的壳,完成该做的动作,直到下班铃响,再带着这身麻木走回家。第二天太阳升起,又会准时杵在工位前,继续当被油裹着的齿轮,没人想逃,也没人知道怎么逃。
有人总说“存在即合理”,可这“合理”到底是啥?是事儿本来就该这样,还是问了没人理、争了被打压,最后不得不认了?你想啊,一种荒唐的规矩要是存在得够久,久到新来的年轻人熬成老师傅,久到心里那点“这不合适”的念头被磨没了,久到天天看、天天做,连别扭劲儿都淡了,它就悄悄变成“常态”了。就像车间墙角那片油污,最开始就指甲盖大一点,没人管,慢慢浸开,最后整个墙面都黑黢黢的,后来的人见了,还以为墙本来就是这颜色。
车间里的人,都被一张看不见的规矩网子捆着。这网子摸不着,可你想张嘴说句“或许能试试别的法子”,喉咙就像被掐了一下;你想动手挪挪工具,让干活省点劲,手就像被拽着。没人敢提异议——在这儿,“提想法”不是“建议”,是“跟规矩对着干”;没人敢改点啥——“改做法”不是“优化”,是“不把权威当回事”。领导从工位旁走过,不管手里的活急不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加快动作;开会的时候,领导说的流程明明有漏洞,底下也只有低头记笔记的沙沙声,连喘气都不敢大声。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倒是有过几个愣头青,想挣开这网子,敢把“不对劲”说出口。可结局早就定了——他们会被贴上“没本事”的标签,有人背后说“连规矩都搞不懂,还敢瞎逼逼”;也会被当成异类,吃饭时没人愿意跟他们坐一桌,休息时没人跟他们搭话,好像他们身上带着“麻烦”,沾着就倒霉。有回老周说“零件顺序调调能省一半时间”,没过两天就被调去上夜班,累得扛不住,没俩月就辞了;还有回小吴说“安全帽带子太松,不安全”,领导却说“你心思咋不放在干活上”,后来小吴也再不提了。慢慢的,敢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一片沉默,跟车间地上积的机油似的,厚得掀都掀不开。
可你要是以为,这股子荒唐劲儿只困在火神重工的铁皮厂房里,就太天真了。它像一滴墨,滴进水里,慢慢散开,其实是整个社会里某类毛病的影子。写字楼里的小年轻,对着反复改八遍的报表,明明知道有更省劲的法子,也不敢吭声,怕被说“不服管”;工地上的老张,看见脚手架螺丝松了,也只敢在心里嘀咕,怕人说他“瞎操心”;就连小区里的大爷,看见垃圾分类站摆得不合理,想提句建议,也先犹豫半天——好像“听话”才是能安稳过日子的法子,“不吭声”才是保护自己的壳。
人啊,慢慢就认了。把“规矩”当成撞不破的墙,哪怕墙是歪的、裂着缝,也不敢碰;把“别惹事”当成过日子的信条,哪怕心里清楚“这样不对”,也不敢说;在定好的框框里缩着身子过,多走一步都怕掉坑里。以前心里还有点火苗,想琢磨个省劲的法子,想改改不合理的地方,想让日子过得顺点——可架不住总有人说“别多事”,架不住每次提想法都被“按规矩来”顶回来,那点火苗慢慢就弱了,凉了,最后彻底灭了。
到最后,就剩一潭死水似的静。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轰隆响,可再也听不见有人商量“咋能更省劲”;工人还在忙前忙后,可眼里再也没了光。那片静里,没了想变一变的念头,也没了敢说句话的劲儿,就剩规矩的齿轮在原地打转,带着所有人,一天又一天,重复着早就写好的日子。
喜欢少女前线:141指挥官请大家收藏:()少女前线:141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