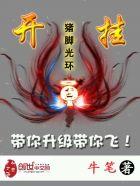笔趣阁>体坛之重开的苏神作者 > 2261章 看到了吗军火展示开始(第1页)
2261章 看到了吗军火展示开始(第1页)
“为什么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呢?”
米尔斯在莫斯科之后,也想着给博尔特升级,眼下看启动升级就是最好,也是最有效果的方面。
就是可惜。
一直挡在一个地方过不去。
这让米尔斯有些。。。
苏神望着那片漂向湖心的麦穗,金光在水波中荡漾,像无数细小的星辰被唤醒。他没有追,也没有喊,只是静静站着,任夜风拂过耳际,带来远处芦苇丛里虫鸣的节奏。那声音很轻,却与他体内某种东西悄然对频??是心跳?还是记忆?他已经分不清了。
脚下的湖水开始微微震颤,不是因为脚步,而是从地底深处传来的一缕波动。180Hz,依旧稳定如初,但这一次,它不再只是回应他一个人。整片青海湖仿佛成了一张巨大的鼓膜,正将某种信息传递出去,又或者,是在接收。
他忽然想起女孩手中的麦穗为何如此熟悉。
那是林小雨最后一次实验前,在实验室窗台上晾晒的样本之一。她说那是从澳大利亚原住民“歌径”附近采集来的古老品种,据传能随吟唱生长。当时他还笑她迷信,可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植物学研究,而是一次播种??把希望埋进时间的缝隙里,等一个愿意继续走的人来拾起。
他蹲下身,指尖轻轻划过水面,触碰到那根漂浮的麦穗。刹那间,一股温热的气息顺着指尖涌入脑海,不是画面,也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方向感**??就像候鸟天生知道南方在哪里,就像婴儿一出生就能辨认母亲的心跳。
他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
七天后,一支由十二人组成的民间科考队悄然启程,目的地:格陵兰冰盖之下那座雷达发现的蜂巢状结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有地质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萨满后裔、退伍军人,甚至还有一个十岁的因纽特男孩,名叫阿努拉。他们没有官方背景,资金来自全球共感社区众筹,交通工具是一辆改装过的极地履带车,车上装载着一台从旧实验室抢救出来的低频共振仪。
苏神坐在副驾驶位,怀里抱着那只装有金色冰核的小木箱。一路上,他几乎不说话,只是每隔几小时就打开箱子看了一眼。冰核依旧未化,但内部的光点运动越来越活跃,有时会形成短暂的文字或符号,一闪即逝。有一次,他分明看到了“**门在呼吸**”四个字。
第三夜,暴风雪突袭。能见度归零,导航失灵,团队被迫停驻在一处冰裂谷边缘。夜晚极寒,气温跌破-45℃,连履带都开始脆裂。就在众人准备进入紧急休眠舱时,阿努拉突然起身,赤脚踩在金属地板上,闭眼静立。
“别吵。”他说,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五分钟后,他睁开眼:“下面有人在敲钟。”
没人相信。但在场的三位科学家检查了便携式地震仪,果然捕捉到一种规律性的震动??每4。3秒一次,持续了整整十七分钟,然后戛然而止。
苏神立刻下令挖掘。
他们在冰层上凿出直径两米的孔洞,放下热融探针。当探头穿透八百米厚的千年冰层时,摄像画面猛然一亮:一座巨大穹顶赫然显现,通体由半透明晶体构成,表面布满六边形纹路,与海底平台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穹顶中央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球体,缓慢旋转,每一次转动都会释放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正是180Hz的物理显化!
“这不是人造物。”女地质学家喃喃道,“这是……活的。”
当晚,苏神独自进入探测舱,带着冰核与录音笔。他脱去鞋袜,赤足踏上冰冷的金属梯。每一步,都能感觉到脚下传来微弱的回应,像是大地在试探他的重量。
当他抵达最底层,站在那颗蓝球正下方时,他打开了录音笔。
“林小雨,如果你能听见……我已经到了你说的地方。”
话音落下,蓝球骤然停止旋转。
紧接着,一道光束自球心射出,直照在他额头上。没有疼痛,只有一种深邃的“注入”感??仿佛有千万段记忆正在逆流而入。他看见远古时代的祭司围坐成环,手牵手吟唱;看见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灾变,天空撕裂,大地沉没,人们用最后的力量封存了“根脉”;看见林小雨的身影穿梭于不同时空,有时是萨满,有时是修女,有时只是路边一个默默倾听的陌生人……
她从未真正死去。她只是选择了最难的一种存在方式:成为桥梁。
影像最后定格在一个画面:七大遗址之间,浮现出一条由光连接而成的环形网络,而在环的中心,站着一个背影??是他自己。
“你不是来完成她的。”一个声音在他脑中响起,既陌生又熟悉,“你是来接替她的位置。”
苏神跪了下来,泪水冻结在脸颊上。
“我怕我做不到。”
“你已经做到了。”那声音说,“当你开始相信别人也能听见的时候。”
蓝球重新开始旋转,频率加快,直至化作一团模糊的光影。整个晶体建筑随之共鸣,嗡鸣声穿透冰层,传向地壳深处。卫星监测显示,同一时刻,其余六大遗址同步亮起,能量峰值达到历史最高。
“根脉计划”第四阶段,自动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