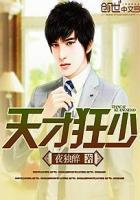笔趣阁>唐奇谭全部角色介绍 > 第一千五百章九章 遭遇(第1页)
第一千五百章九章 遭遇(第1页)
午后的广州市舶司门前,正是人声鼎沸的时节。青石板路被往来行人踩得光滑,两侧商铺鳞次栉比,幌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最多见的绸缎行的幌子上,用明艳的丝线绣着“云锦”“蜀锦”“春彩”“白叠”字样。
在街。。。
秋深霜重,太湖畔的芦苇荡泛起层层银白。晨雾未散,湖面如镜,倒映着远处几间茅屋,檐下挂着一串风干的艾草,随风轻晃。柴翁居依旧静谧,唯有院中石磨旁一只铜壶正咕嘟作响,热气袅袅升腾,混着茶香弥漫在空气里。
苏寒烟坐在廊下,手中摩挲着那支旧笔,笔杆已被岁月磨得光滑温润。她目光落在案上未完成的半句遗言??“若有一天火柴燃尽,自有星火燎原。”这是裴昭最后的气息所托,也是他一生信念的凝结。她不曾将它刻碑立传,只悄悄抄了数十份,寄往各地共读堂、私塾与律评会,附言:“此非训令,乃念想耳。”
门外脚步??,是律和回来了。他已三十有五,鬓角微霜,却仍穿着粗布短褐,肩头还沾着北地风沙。他是裴昭收养的孩子中最倔强的一个,十年前执意北上塞外,在敦煌主持新设的“识字驿”,专为戍边将士及其家眷讲授《承平律》与基础识字课。此次回乡,是因江南诸州联合发起“万童书律”大典,邀他作为代表返乡主祭。
“阿娘。”律和跪坐在蒲团上,声音低沉而稳,“敦煌那边都安顿好了。今年又有三百孩童能背全《权利篇》,连胡商之子也学会了写‘告官’二字。”
苏寒烟点头,端来一碗热粥:“你父亲若还在,定要说一句:‘一字入魂,胜过千军。’”
律和苦笑:“可如今有人开始说,《承平律》太过激进,该当删减几条,尤其是‘民可诉官’那一章……前日我路过苏州府学,听见几位老儒议论,说我们教得太快,乱了纲常。”
“纲常?”苏寒烟冷笑一声,眼中寒光乍现,仿佛又变回当年斩断霍延年佩剑的那个女子,“他们口中的纲常,可是让佃户跪着交租、妇人不能立契、罪囚家属连坐的‘常’?你父亲用命换来的不是妥协,而是破局。你们这一代人,若连这点胆气都没有,就配不上那盏灯。”
律和低头不语,良久才道:“可百姓终究怕官。前些日子,浙东有个村妇状告县令强征粮税,结果状纸刚递上去,家里就被烧了。虽然后来律评会介入,逼得官府赔银抚恤,但她再不敢出庭。”
苏寒烟站起身,走到墙边取下一卷黄绢,缓缓展开,竟是当年裴昭亲笔誊写的《两仪同命》残卷节选。她指着其中一行字:“你看这里??‘律行于弱者之手,方显其真;若仅强者执之,则名为律,实为枷。’这便是核心。我们教人识字,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看得懂告示,更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权说话,有权质疑,有权站出来指认不公。”
她顿了顿,声音渐柔:“你记得小时候问过你父亲,为什么非要让人人都识字吗?他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条河,河水浑浊,岸边百姓饮之皆病。官府说这是天灾,无药可医。后来来了个游医,教会大家用纱布滤水,并写下方法贴在村口。三年后,此地再无人因饮水致病。你说,这纱布值钱吗?不值。但它救了多少命?”
律和眼眶微红:“所以识字,就是那块纱布。”
“正是。”苏寒烟轻轻抚过卷轴,“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在每一条河流边,放上一块干净的布。”
数日后,苏州城外百亩空地上搭起高台,彩旗猎猎。“万童书律”大典如期举行。来自十三州的三千名七至十二岁的孩童齐聚于此,每人手持一支竹简笔,面前摆放一方小砚。随着司仪一声“开卷”,孩子们齐声朗读《承平律》第一章,稚嫩的声音汇成洪流,震彻云霄。
>“人生而平等,无论贵贱男女,皆享自由之权,受律保护之责。违者,天下共击之。”
随后,他们提笔书写,一笔一划,极为认真。这些孩子中,有的是农夫之女,有的是船工之子,甚至还有南迁胡族的后代。他们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宣告:未来不属于世袭与特权,而属于每一个愿意学习、敢于发声的人。
就在此时,一骑快马自北方疾驰而来,尘土飞扬。马上之人身穿黑袍,胸前绣着一朵银线梅花??那是议事阁密使的标志。他翻身下马,直奔主坛,将一封火漆密信交到律和手中。
信是长安来的,署名是一位退隐多年的老御史,曾参与起草初版《承平律》。信中写道:
>“宫中有变。皇帝病危,太子软弱,权臣萧氏欲借机摄政,已暗中下令废止‘民间讲律’之令,并拟查封全国共读堂,称‘聚众议律,易生悖逆’。另遣心腹接管宣律使系统,意图重塑律法解释权。此令尚未明发,然风声已泄,恐不出月内即行推行。望速议对策,勿使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全场骤然寂静。原本欢腾的气氛瞬间冻结,如同春日突降暴雪。
律和握信的手微微颤抖。他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争,而是一场对“识字新政”根本理念的全面反扑。若任其得逞,则所有共读堂将成为非法组织,所有宣律使沦为叛逆,千万孩童刚刚点亮的心灯,或将再度陷入黑暗。
当晚,柴翁居灯火通明。律和、律平(现任江南律评会会长)、律明(蜀中义学总教习)三人齐聚,另有六位来自不同州郡的代表连夜赶来。苏寒烟坐于主位,虽年逾古稀,眼神却锐利如刀。
“怎么办?”有人低声问,“我们没有兵,也没有官印,如何对抗朝廷诏令?”
律明冷声道:“那就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权力不在紫宸殿,而在万家灯火之间。”
苏寒烟缓缓开口:“你们还记得‘律鸣之夜’吗?那天,裴昭以身为引,将力量注入地脉,唤醒了十七座共读堂。今日,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待谁来点燃火焰,而是让每一盏灯自己燃烧起来。”
她起身,取出一张地图铺于桌上,正是全国共读堂分布图。百余个红点遍布南北,犹如星辰罗列。
“明日开始,所有共读堂同步授课,内容不再是《权利篇》,而是新增一章??《抗令三策》。”
众人一惊。
“第一策:凡遇查封,不得抵抗,但须全体静坐诵律,直至官员离去;第二策:每堂录下当日课程,由信鸽或商队送往邻州,确保信息不断;第三策:发动学生家长联名具保,声明自愿参与讲律,责任自负,与他人无关。”
她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要让他们看到,这不是造反,而是守法。他们若敢动武,便是践踏‘民不受非法拘捕’之条;他们若下诏禁止百姓识字,则自身已先违律。”
会议持续至天明。最终决议:七日内,全国共读堂统一行动,称之为“明烛行动”??寓意“黑暗愈浓,烛光愈明”。
消息一经传出,响应如潮。河北某村,八十老翁拄拐带领全村老少跪读《承平律》,声称“吾辈虽愚,亦知何为公正”;岭南山区,数百名妇女组成“巾帼书社”,日夜抄写律文,分发邻里;就连远在西域的敦煌识字驿,也在风沙中升起一面白幡,上书八个大字:“人在律在,寸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