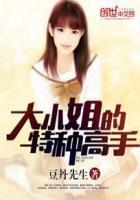笔趣阁>且隋万事顺安什么意义 > 第282章 东西(第1页)
第282章 东西(第1页)
一
反王联盟当初进入大兴城太过“顺利”,目光尽被帝都的虚名与财富所眩,竟未能及时、彻底地掌控那些真正扼守关中气运的“锁钥”——东面雄峙的潼关、东南屏障武关、蓝田关,西南门户大散关、骆谷关,西北咽喉陇山关……
这些雄关险隘,大多仍牢牢掌握在忠隋将领或已被杨子灿暗中控制的军镇手中。
反王们仅仅因为进军路线与确保退路的考量,控制了蒲津、龙门等少数黄河渡口,并派驻重兵。
他们或许还在庆幸保留了这条北归“生命线”,却未曾深思,这是否是那位远在洛阳的魏王,为了让他们安心在关中这口大锅里内斗,而故意留下的、涂满蜜糖的陷阱?
这条看似安全的退路,或许在最终时刻,将成为焚烧他们野心的最后一把火。
于是,无形的战争机器开始轰鸣:
江南大营数万精锐,搭乘隋通船运的巨舰,溯江西进,转入汉水,像一把沉默的尖刀,悄无声息地抵近秦岭东南麓的武关……
山东剿匪大营的铁骑,在荡平群寇的锐气加持下,卷起烟尘向西滚滚而去,兵锋直指蒲津、龙门,凛冽的杀气隔河已让对岸的守军感到寒意……
河南剿匪大营的健儿,沿崤函古道稳步西推,与潼关守军互为犄角,如同一道缓缓升起的闸门,封死了关中正东……
河西走廊剿匪大营鱼俱罗部与天水屈突通部,则两线对进,像一把巨大的铁钳,开始合拢于陇山、大散关一线,意图彻底断绝关中与陇西、巴蜀的联络……
一张由精兵强将构成的死亡之网,正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着关中,向着那座沉浸在权力迷梦中的大兴城,稳健而冷酷地合拢。
空气中的平静,已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假象。
二
当东都紧锣密鼓布下天罗地网时,大兴城这边,经过连日仓促不堪、甚至可称狼狈的准备,新皇杨侗的登基大典,终于要在一种极其窘迫和尴尬的氛围中,勉强登场。
国号依旧为“隋”,改元“延兴”。
然而,这场本应彰显新朝气象、威加海内的盛典,却处处透着捉襟见肘的寒酸。
宫阙虽在,内里却被搬空大半,显得空荡而寂寥;礼器残缺,多是前朝库底翻出,仓促擦拭,难掩陈旧;乐班七拼八凑,音律参差,奏不出盛世华章;最要命的是操持大典的礼官与有经验的官员,要么随驾东都,要么老迈昏聩,要么已成了刀下之鬼。
筹备过程混乱如粥,李渊、李密等人忙于暗中布局与权力交换,对此乐见其成,恨不得大典越潦草越好,方能凸显杨侗不过是个傀儡。
卫玄有心无力,急得嘴角燎泡。
李秀宁身份敏感,纵有能力,亦不便过多插手。
就在这几乎要沦为天下笑柄的关头,一人越众而出,以惊才绝艳之术,稳住了这摇摇欲坠的局面。
此人便是李渊新近发掘并引为心腹的年轻谋士,李淳风。
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生于仁寿二年。其父李播,学究天人却厌弃官场,弃官为道,自号“黄冠子”,尤精天文历算。
家中藏书半屋皆是星表、算经。李淳风幼承家学,天资卓绝,十岁能熟背《九章算术》,十二岁便可摆弄家中那具汉代旧浑仪,对其结构原理了然于胸,被视为“活算盘”。
年方十五,便入终南山静云观,表面修道,实则在清幽之地遍览天文、易数典籍,更动手改良观中观测仪器——彼时埋下的种子,正是后来那惊世“三辰仪”的雏形。
后因杨玄感事受牵连,遁入终南深处,直至李渊太原起兵,在南下途中其才被刘文静惊为天人,直接荐入秦王府为记室参军,掌文书兼“望气”、“择日”。
不久,其才具更得李渊本人赏识,虽年纪尚轻,已擢升为高级幕僚,参赞机密。
李淳风出身“历算科”,师法刘焯、张宾一脉的《皇极历》学,乃根正苗红的官方“天算学派”。
他笃信“擎天算数,可验于天”,极端注重实际观测、仪器精度与历法验证,走的是一条以数理擎天、追求客观规律的实证道路。
其未来名垂青史的《麟德历》、《乙巳占》,皆是强调严密推算、可经实践反复检验的数理巨着。
此刻,面对这混乱如麻的登基筹备,李淳风展现出了他迥异于常人的严谨与务实。
他不需要那些虚浮的排场,所倚仗者,不过是手中星盘、临时寻来的堪用浑仪,以及胸中包罗万象的精密算学。
吉时吉日?他仰观天象,俯察历法,推演得精确至刻,不容毫厘之差。
仪仗流程?他参照古礼,削其繁枝,存其主干,结合现有条件,制定出效率最高、漏洞最少的方案,每一步皆有章法,每一环皆扣准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