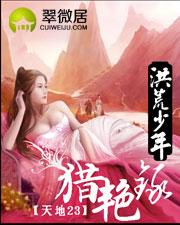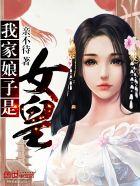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一共多少章 > 第450章 来得比他这个当爹的还快(第2页)
第450章 来得比他这个当爹的还快(第2页)
至第九十七名时,天已全黑。海风骤紧,银棠树发出呜咽之声,树干裂开一道缝隙,流出的不再是金色汁液,而是一缕缕淡蓝色雾气,凝聚成人形轮廓??一个少女模样,赤足披发,手中抱着一只破陶罐。
她开口,声音像是从海底传来:
“你们……终于来了。”
沈明远颤声问:“你是林六娘?”
她摇头:“我是她们所有人。我是被大海吞没却无人呼唤的名字,是沉在深渊里不肯离去的回声。我们等了百年,只为这一刻。”
“为何选在此地?”
“因为这里不是陆,也不是海,是生与死之间的缝隙。凡被遗忘者,魂无所归,便随洋流漂至此岛。我们守着这块无字碑,只盼有人听见。”
沈明远望向那碑,忽然明白:它并非无字,而是等待被填满。
他转身对弟子们说:“取陶瓮来。”
灰烬倾出,与海沙混合,涂于碑面。刹那间,整座岛屿震动,银棠树根部迸发光芒,无数细小身影从沙中升起??有孩童牵母衣角,有老人拄杖远眺,有女子怀抱婴儿,有少年背负行囊。他们不哭不闹,只是静静看着那块碑,眼中含光。
沈明远执笔,以血为引,开始誊录。每一笔落下,便有一道光影融入碑中,石质由灰转暖,泛出玉色光泽。当第九百九十九个名字刻完,碑顶忽然生出一朵四色花芽,缓缓绽放。
花心之中,浮现出一行新字:
**此处即归途,非因神迹,乃因有人愿记。**
那一夜,岛上彻夜明亮。海面萤火浮动,天空星河倒悬,人影与光影交织共舞。沈明远疲惫至极,倚树而眠。梦中,他见念棠先生立于舟头,手持棠枝笔,微笑不语。身后波涛汹涌,却无一字沉没。
醒来时,东方既白。银棠树已不见,唯余石碑矗立,碑文密布,却无一人能尽数读完??因名字随观者心意流转,每人所见不同。老渔夫见的是亡妻之名,年轻弟子见的是早夭胞妹,而沈明远所见,竟是自己祖父沈砚之侧,多出一行小字:
**沈明远,十六岁,守丧七日,首启新录。**
他猛然惊觉:原来他们也在被记住。
返程途中,风暴再起,但小舟稳行如初。归名潭灰烬所剩无几,却在船尾自行增生,仿佛吸收了海上魂息。更奇者,舟过之处,海水泛起淡淡金纹,数日后沿海居民纷纷报告:滩涂上自发长出棠树幼苗,皆开四色花,且朝向书院方向倾斜生长。
三月后,春分将至。书院重开讲席,沈明远将此次南行所录编为《沉魂录拾肆?海裔篇》,并附《忘忧碑拓本》一份,呈送礼部备案。皇帝览毕,久久不语,终提朱笔批曰:
**天下之痛,不在疆域,而在遗忘。此碑当为万世镜鉴。**
与此同时,民间已有传言:只要在海边点燃纸灯,写下欲念之名,投入海中,若灯火不灭反逆流前行,则说明那人魂已得安,正在回应。
某夜,江南一户人家,母亲焚灯祭子。孩子七岁溺亡,生前最爱吃桂花糕。灯漂出十里,忽停于一处浅湾,周围浮起数十朵野棠花,围成一圈,花心各嵌一小块风干桂花糕。
她跪地痛哭:“儿啊,你尝到了吗?”
风拂水面,花瓣轻颤,拼出两字:
**甜的。**
又有一日,西域商队穿越戈壁,夜宿废堡。首领梦见一女子递来一碗清水,说:“喝了吧,你不该死在这里。”惊醒后发现帐篷外真有一陶碗,盛满清泉,碗底刻着“苏兰娘”三字。众人焚香叩拜,翌日竟寻得古道遗迹,得以脱困。
阿禾得知此事,亲赴南疆,在苏兰娘化身为棠之处立碑,并奏请朝廷设立“巡名使”制度,专司搜录史册不载之亡魂。她走遍瘴疠之地,曾在暴雨中跪守三日,只为听清一位垂死老妪断续说出的族人名单;也曾潜入塌陷矿井,借萤火虫照明,抄录墙上矿工以指甲刻下的遗言。
十年光阴流转,第十八册《沉魂录》问世,封面以海贝、陶片、布缕与骨粉压制而成,谓之“百物书”。其中不仅录名,更附各地风俗、方言、歌谣、手艺,皆为濒临失传之遗响。学者称:“此非仅赎魂之录,实为一部活着的民史。”
而那株老棠树,愈发苍劲。每逢春雷炸响,树皮裂缝中不止生出石碑结晶,更有完整竹简缓缓挤出,上书陌生篇章。经考证,竟是失传已久的《列子?汤问》佚文、汉代乐府残章、唐代边塞日记片段……内容皆与“记忆”“呼唤”“回应”相关。
最惊人者,乃一段战国竹简,记载齐国盲乐师钟离春事迹。其文曰:“春少孤,习埙于野。每奏,百鸟停鸣。临终言:‘吾声虽绝,必有继者。’葬后三年,邻童忽能吹古调,自称‘钟离附体’。里人异之,建祠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