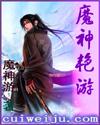笔趣阁>华夏真品阁网上商城 > 第二十一集 从珂哭城(第2页)
第二十一集 从珂哭城(第2页)
安重诲威慑百官,明宗也自畏他三分。
夏州刺史李仁福得知明宗好鹰,便派人送来白鹰,安重诲拒绝收纳。明宗却派人将白鹰悄悄带回宫中,后至京城西郊嬉戏,不免心有余悸,对随从说道:勿使安重诲知也。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自此言可知,安生诲已犯天子忌讳。
另外安重诲虽然勤政,却亦不免欺君擅权,对其心腹偏听偏信,竭力袒护纵容。因其权倾朝野,连皇子李从荣、李从厚都敬事不暇。
明宗使养子潞王李从珂任河中节度使,安重诲善于洞察,谓其非天子亲生,手握重兵易生野心,日后必为国家隐患;便以内调为名,以夺其军权。
乃矫造诏书,唆使潞王府旧将河中牙内指挥使杨彦温,趁便驱逐节度使李从珂。
杨彦温知道安重诲在朝中炙手可热,不敢得罪,于是满口应诺,打发来使回报。
字幕:西元九三零年,唐明宗长兴元年。
李从珂出城,检阅战马。杨彦温趁机关闭城门,不许李从珂入城,逼其返回洛阳。
李嗣源闻报河中生变,便将李从珂召回朝中,另行安置。
安重诲又唆使宰相纷上奏疏,请朝廷追究李从珂失守河中之罪,欲趁机除掉李从珂。
李嗣源知道此皆是安重诲北后指使,乃驳回一班宰相奏议,只命李从珂暂时赋闲在家,不先予安排职爵,并欲派人招降杨彦温。
安重诲则力主用兵,派侍卫指挥使药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讨伐。临出兵时又密嘱二将:务必斩杀杨彦温,不可留其活口。
二人领命,引兵而往,果然旗开得胜,斩杀杨彦温,函其首级而还。
安重诲复奏李从珂部将谋反,主将亦其失职,应予从重处置,以求除恶务尽。明宗闻奏大为不悦,君臣言辞之间激烈冲突,从此二人生隙。
后来禁军将领李行德、张俭上书弹劾:安重诲私募士卒,整械备装,图谋不轨。
此事后经查证,实为诬陷。李嗣源虽以诬告之罪将李行德、张俭族诛,但也对安重诲起了猜忌之心,命范延光同任枢密使,以分散安重诲权力。
安重诲亦觉自己威震人主,欲图急流勇退,接连申请辞职,终被批准外放河中节度使,再以太子太师闲职,致仕在府。
明宗恐其心怀异志,命义子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以监督安重诲,并使步军指挥使药彦稠率军前往河中。
李从璋早就怀恨安重诲,即派重兵冲进安府,以大棒猛击安重诲夫妇头部,致其惨死。安重诲被杀之时,便知自己已为天子所弃,遂大声疾呼道:臣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李从珂,他日必为朝廷之患也!
李嗣源闻其临终之语,为安抚李从珂,下诏为安重诲定罪。
安重诲既死,唐明宗复召范延光与赵延寿为枢密使,同掌朝政。
忽一日君臣议政,明宗便问范延光:我全国各地,饲养战马,其数几何?
范延光奏道:有骑军三万五千。臣尝计算一马之费,可养步卒五人,三万五千匹马,即可抵十五万兵之食也。
明宗叹道:肥战马而瘠军人,此朕所愧对将士也。
于是忽想起当年逼迫正副指挥使造反的魏博银枪效节军,不由出了一身冷汗。遂与范延光商议,遗使前至邺都,下密诏于银枪效节都节帅赵在礼,如此如此,永除后患。
赵在礼不敢抗命,遂依皇帝毒计,尽出府库犒赏三军,诱使帐下九名指挥使分率八千效节军,北戍卢台。银枪效节军在北上途中,却钻入唐明宗所设埋伏,将此军联同随营家属并皆处斩,浮尸塞河,永济渠为之变赤。
这支杨师厚所创牙兵,经此杀灭之祸,魏博牙兵跋扈之迹在史籍记载中便很少见到。
唐明宗以诡计灭了银枪效节军,节帅赵在礼被授同州节度使,自此效节军不复存在。但八千将士及万余家属冤魂便永为恶梦,缠绕赵在礼心头,终生而不得去。
同时因无魏博精骑屯守幽、涿二州,其北面契丹及西面党项二族便迅速坐大,成为此后历代中原皇帝心中忧患。
镜头转换,契丹辽国,天显元年。
辽太宗耶律阿保机东征渤海国,先集中全部兵力,攻下西部重镇扶余城,后又围攻首都忽汗城。国王率群臣开城投降,辽国就此统一渤海全境。
阿保机将渤海改为东契丹国,以皇太子耶律倍任东丹王。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置官府,从而结束唐末以来辽东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统一。
七月二十七日,阿保机在还都途中病逝,终年五十五岁,谥号升天皇帝,庙号太祖。
阿保机因在班师返回契丹途中突然病逝,并未交代身后承嗣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