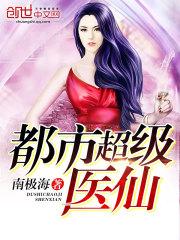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原著叫什么名字 > 第444章 要在打猎杀父王才比较好玩吗(第2页)
第444章 要在打猎杀父王才比较好玩吗(第2页)
此举初时遭人不解,甚至有官府派人质询,谓“惑乱民心”。沈砚只淡淡回应:“若民心本乱,非因我说话,而因他们太久无人倾听。”
渐渐地,人们开始习惯这一仪式。有人写下对战死兄弟的歉意,有人追忆早夭的儿女,更有年轻女子焚去一封未曾寄出的情书,附言:“我不怨他负约,只愿他知道,我曾真心待他。”
这一年夏至,天降甘霖,连旱三月的北方终于解渴。百姓传言,是“知棠显灵”。沈砚听闻,只是笑了笑。他知道,真正的甘霖不在天上,而在人心之中。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未止。
某夜暴雨倾盆,雷声震耳。一名少年冒雨叩门,浑身湿透,面色惨白。他是附近山村的猎户之子,来求沈砚救命。原来其父半月前进山打猎,误入一处废弃古庙,拾得一枚铜铃,带回家中悬挂于梁。自此家中怪事频发:夜半铃响无人触,灶火自燃又熄,幼妹每晚惊叫“有人站在床边”。
最可怕的是,父亲日渐萎靡,眼神涣散,口中喃喃:“我不是故意的……当年若救她出来,也不会……”
沈砚闻言,神色骤凝。他问:“那庙在何方?”
“在断龙谷深处,据说百年前曾是尼庵,后来一场大火,烧死了十几个女子,从此无人敢近。”
沈砚当即收拾药箱,不顾风雨,随少年连夜出发。山路泥泞难行,雷电交加,途中几次险些滑坠深渊。弟子劝阻,他却道:“有些声音,只能趁风雨之夜才能听见。”
抵达古庙时,已是丑时。庙宇坍塌大半,唯有正殿尚存,梁上果然悬着一枚青铜铃铛,样式古旧,表面刻有细密符文,隐约可见“赎”“忆”二字残痕。
沈砚仰头凝视,忽然心头一震??这铃,竟是知心书院失传已久的“引魂铃”,传说为初代知棠所铸,能召沉冤之魂现身陈情。后因威力太强,易引执念反噬,遂被封存。怎会流落至此?
他伸手欲取,指尖刚触铃身,耳边骤然响起无数女子哭声,凄厉如刀割耳膜。眼前景象突变:烈焰冲天,十余名青衣女子被困殿内,拍门呼救;门外一群村民持棍守候,高喊“妖孽当诛”“淫寺必毁”;一名年轻男子跪于阶前,痛哭乞求开门,却被众人按倒在地……
画面一闪,又见那男子多年后成为村长,每逢清明必独自来此烧纸,却从不提当年之事。直至临终前一夜,他突然坐起,嘶声道:“我对不起净尘……她说等我娶她,我答应过的……”
沈砚猛然抽手,铃声戛然而止。
“净尘?”他低声自语,“原来如此。”
他转身问少年:“你父亲,是不是姓张?”
少年震惊:“先生如何知晓?”
“因为他梦见的不是鬼,是他祖辈的罪。”沈砚叹息,“这座庵,并非淫寺,而是孤女收容之所。那些女子,皆是战乱中失去亲人的流民,由一位法号‘净尘’的女尼收留。后来有人诬告她们勾结叛军,煽动村民纵火封门。唯一逃出的,便是你曾祖父??他曾与净尘互许终身,却因怯懦未敢相救。”
少年跪地痛哭:“那……我们张家,岂非世代背负血债?”
“不。”沈砚扶他起身,“血债需偿,但方式不是以命抵命,而是以记忆赎回遗忘。你们欠她们一句公道的话。”
当即便命少年取清水洒净庙宇,在废墟前设香案,摆素果,点七盏油灯。沈砚亲自执笔,写下:
>断龙谷旧尼庵诸位亡灵:
>
>汝等无辜罹难,名姓几近湮灭。今由沈砚代述:尔时有女尼净尘,收孤抚弱,行善积德;有少女十一人,名不可考,皆因战火失所,托庇于此。三百年前六月初三夜,遭诬陷焚身而亡,尸骨无存,冤屈未雪。
>
>今有张氏后人张某,代先祖忏悔,不敢求恕,唯愿铭记。特立此碑文,诵名一遍,焚香九柱,愿诸魂得释,早登彼岸。
念毕,火光腾起,照亮残垣断壁。刹那间,风雨骤停,云开月出。那枚铜铃轻轻一震,自行脱落,落入火中,发出一声清越长鸣,宛如叹息。
次日清晨,少年来报:其父昨夜安眠,醒来第一句话便是:“我去见过净尘了……她说,她一直都知道我没能救她,但她不怪我爹,只希望有人记得她活过。”
沈砚点头:“这才是真正的疗愈。”
归途上,弟子不解:“先生,若天下处处皆有此类旧怨,您一人如何走得完?”
“我走不完。”他望着远处青山,“但我可以教会别人怎么走。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都是新的知棠。”
数月后,北岭村传来消息:村中已为阿禾立碑,且每年清明设“无名席”,全村共祭。更令人欣慰的是,那名曾多次流产的妇人顺利产下一女,取名“念安”??不忘过往,心有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