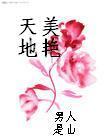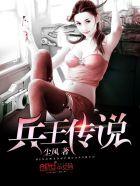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泥白佛笔趣 > 第493章 堂妹变小姑了你说这事儿整的(第2页)
第493章 堂妹变小姑了你说这事儿整的(第2页)
>现在我终于想通了。我不是逃兵,我只是另一个活下来的人。我想把我的故事说出来,也为林小梅说。”
孟波立刻安排团队前往昆明。见面那天,陈秀兰穿了一件藏青色列宁装,胸前别着一枚早已停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章。她的双手布满老年斑,但握笔的姿势依然稳健。
“我们那个医疗所设在山洞里。”她缓缓开口,“三面岩壁,一面帆布挡风。零下三十度,水一泼就结冰。伤员太多,我们只能把重伤员放在中间,轻伤员靠外取暖。夜里,我就守在炉子边烧热水,给战士们化冻伤口上的血痂。”
她说起林小梅,眼里闪着光:“她是上海人,话软,心硬。有一次炮弹炸塌了洞口,她背着两个伤员爬出去,膝盖全磨烂了,回来还笑着说:‘没事,我皮厚!’”
“她牺牲那天,是我离开后的第三个月。敌机突袭,她本可以躲,但她冲回去抢运药品,被炸死在药房门口。战友们说,她怀里还紧紧抱着一支胰岛素针剂??那是给一个糖尿病重伤员准备的。”
陈秀兰说着,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整齐码放着几十张泛黄的照片、日记本、勋章复印件。最底下是一张黑白合影:一群女医护站在雪地中,笑容灿烂。她指着其中一个短发姑娘:“这就是林小梅。我想让她出现在你们的镜头里。”
节目组将这段口述制成特别短片,命名为《未完成的使命》。上线当天,评论区涌入上千条留言:
>“我外婆也是战地护士,她从来不说,直到看到这个视频才流泪。”
>
>“我爸是老兵,看完拉着我妈的手说:‘你当年也不容易。’”
>
>“原来英雄不只是冲锋陷阵的人,还有那些默默递上纱布的手。”
与此同时,《大地留痕》项目正式启动。孟波组建了一个由历史学者、民俗专家、青年志愿者组成的百人团队,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对全国五千名八十五岁以上老人的口述采集。
他们在山西找到了曾参与修建红旗渠的女石匠赵桂香。八十九岁的她仍能挥动锤子,在石头上凿出“自力更生”四个大字。“那时候一天干十二小时,手上全是血泡。领导说让女同志歇两天,我们不干。我们也要为子孙后代凿出一条活路!”
在安徽凤阳,他们见到了大包干前夕带头按手印的十八户农民之一的女儿??六十七岁的吴月琴。她保存着父亲当年那份摁着红手印的“生死状”复印件。“我爸说,签这个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但他还是按下去了。他说:‘穷怕了,再不拼一把,娃都没饭吃。’”
在海南文昌,他们采访了新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培训班的学员王亚妹。如今已九十一岁的她还记得当年毛主席接见她们时说的话:“妇女解放,要从方向盘抓起。”
“我们开着拖拉机绕天安门转了一圈。”她笑着回忆,“全国人民都在喊‘铁姑娘’,可我觉得,我们不是铁做的,我们是有血有肉的女人,只是不想再被人当成弱者。”
这些故事被整理成系列专题,在央视科教频道滚动播出。教育部将其纳入中小学思政课辅助教材;国家图书馆设立“平民记忆特藏室”,永久保存所有原始音视频资料;多地博物馆相继举办“无名者之光”巡回展览。
更令人动容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动走进乡村,倾听祖辈的故事。
一位北京大学生利用暑假回到河南老家,记录爷爷作为知青下乡修水利的经历。他发现,老人床下藏着一本日记,里面写着:“今天挖渠十米,累得吐血。但想到将来能浇灌万亩良田,值了。”
他将日记录入电脑,配上老照片,做成H5页面发布在网上,三天转发超百万。
一位广州女孩帮奶奶整理旧物时,发现一叠泛黄的信件。那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身为铁路工人的爷爷参与救援时写的家书。“路面裂开像大嘴,火车脱轨翻进沟里。我们用手扒,用肩扛,救出二十三个人。有个孩子抱着我不撒手,喊我爸爸……我没敢告诉他,我自己的儿子还在兰州上学。”
女孩把信读给班级同学听,全班沉默良久。班主任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课。”
孟波受邀在清华大学演讲。站在讲台上,他没有用PPT,只带了一只旧录音笔。
“这是我从周秀兰老人那里借来的。”他说,“她说,这是她当年在战地记录伤员信息用的。现在它录满了上百位老人的声音。”
他按下播放键。
先是周秀兰哼唱的那首《雪落长津湖》,接着是马金花扫地时的咳嗽声,吉克阿依讲述往事时的笑声,韦玉梅摩挲电码本的摩擦声,陈秀兰说到林小梅时的哽咽……
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一阵风吹过旷野,又像春雨落在泥土上。
“我们总以为历史是由重大事件构成的。”孟波望着台下数百双年轻的眼睛,“但真正支撑起时代的,是这些细微的声音。它们不属于头条,却构成了民族的呼吸。”
演讲结束,掌声久久不息。一名学生举手提问:“我们普通人,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孟波回答:“你愿意坐在这里听一个老人的故事,就已经在改变了。”
那天晚上,他独自走在校园林荫道上,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阿水婆发来的语音消息,背景是海浪声。
“小孟啊,今天又有学校的孩子来看我。他们问我,如果国旗掉了怎么办?我说,那就捡起来,再升一次。只要人心不倒,旗就不会落。”
他抬头望向夜空,繁星如织。
他知道,这场旅程不会结束。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那些深埋于泥土的记忆,正一寸寸苏醒。它们不再沉默,也不再孤单。
因为在某个城市的书房里,有个少年正一笔一画抄写祖父的日记;在某个村庄的火塘边,有个女儿正为母亲录音讲述青春;在某个大学教室里,有个老师正播放一段关于无名烈士的影像……
他们亦曾年轻。
而今天的我们,正在学会如何真正地看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