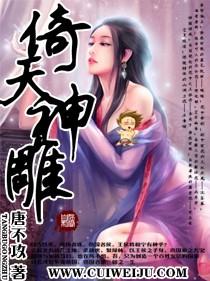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结局完整版 > 第1168章 小锦我好想你(第2页)
第1168章 小锦我好想你(第2页)
他从怀中取出一卷竹简,焦痕遍布,边角蜷曲,显然曾经历烈火焚烧。但上面仍有字迹残留,用朱砂与血混合书写,笔力苍劲。
“这是……?”阿芜伸手接过。
“《民忆录?续编卷一》。”他说,“我在牢里写的。用指甲刮墙灰混唾液,写了三年。后来被狱卒发现,打断了两根肋骨,烧了一半。剩下的,我吞进肚子里,靠记忆活下来。”
阿芜颤抖着展开竹简,目光扫过那些歪斜却坚定的字迹。她读到了一名女子为保族谱跳井自尽;读到了三位孩童冒死藏匿一本童蒙识字书,只为记住祖先的名字;读到了一位盲眼老琴师,临终前弹完最后一曲《忆归》,琴弦崩断时口中喃喃:“听见了吗?那是我们的声音。”
泪水无声滑落。
她终于明白,为何自己能在回音谷听见千万人的低语。
因为这些人,从未真正沉默。
他们用最卑微的方式,守住了最不该丢失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早送来?”她哽咽。
“送不到。”裴砚冷冷道,“净魂司的眼线遍布天下。我若现身,必遭围捕。而你一旦接触此物,也会被感知。所以我只能等??等你主动走出书院,等你踏上寻忆之路,等你成为他们共同呼唤的名字。”
阿芜低头看着竹简,忽然笑了:“你说你还债……那你可知,我母亲临死前写的‘忆契咒’,最后那一句是什么?”
裴砚皱眉:“我不知道。”
“不是‘归来’。”她轻声说,“是‘宽恕’。”
空气骤然凝滞。
风雪再次涌动,却绕开两人,仿佛天地也在屏息。
“她写下的是:‘若天下共忆,则吾女归来;归来非为复仇,乃行宽恕之道。’”阿芜望着他,“所以,我不是来清算过去的。我是来终结遗忘的循环。”
裴砚怔住,眼中闪过一丝痛楚。
他曾是净魂司最年轻的统领,奉皇命清理“悖逆之籍”,亲手焚毁数百藏书楼,斩杀数十史官家族。他以为自己在维护秩序,实则成了屠戮记忆的刽子手。直到某一日,他在一堆灰烬中捡起半片残页,上面写着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和生日??那是他妹妹,因患疫病早夭,却被朝廷下令抹去所有记录,只因她出生那年,民间有谶言称“女婴降世,将启乱兆”。
他开始怀疑。
然后反抗。
最终背叛。
“你觉得,我能被宽恕吗?”他低声问,声音几近破碎。
阿芜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将竹简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走向他,伸手触碰他空荡的右袖。
“你的手臂不在了。”她说,“可我记得它曾写下多少名字,救下多少残卷。我也记得你在雪地里对我说:‘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哪怕脏了手。’”
她抬头看他:“你要的不是我的宽恕,是与你自己和解。”
裴砚猛地别过脸去,喉结剧烈滚动。
就在此时,庙外忽传来一阵脚步声,细碎而急促,像是孩童奔跑。紧接着,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阿芜姐姐!”
小满冲了进来,怀里紧紧抱着一本湿漉漉的册子,头发滴着水,脸颊冻得通红。她身后跟着几名共忆村的孩子,每人手中都捧着陶片、木简、布帛,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我们……我们追了好几天!”小满喘着气,“昭树下的灯突然灭了,然后紫花开出了黑色花瓣!我们听见有人在喊你!”
阿芜快步上前,扶住她:“你们怎么敢一个人来这种地方?”
“因为我们记得啊!”一个小男孩大声说,“你说过,只要有人愿意听,故事就不会结束!所以我们带来了新的记忆!”
孩子们纷纷上前,将手中的物件递出。一块陶片上刻着:“我爷爷说,他曾在宫墙外听见一个小女孩哭,说‘妈妈,我想回家’,可没人理她。”
一张羊皮纸上写着:“我娘临死前告诉我,她本姓吴,祖籍江南,父亲是个抄书匠……”
还有一块木牌,用炭笔画着一个女人抱着婴儿站在火堆前,旁边写着:“这是我梦见的姑奶奶,她说她的名字叫素心。”
阿芜一一接过,指尖抚过那些粗糙的字迹,心口滚烫。
这些不是历史,是活着的证言。
它们不成体系,不求完整,甚至真假难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