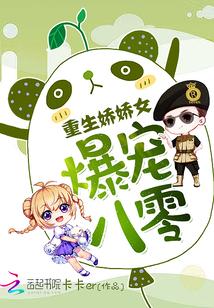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结局完整版 > 第1170章 所谓三国联军(第2页)
第1170章 所谓三国联军(第2页)
柳知言怔住。
原来这些年,他一路埋种,早已在民间激起涟漪。许多村庄自发组织“守忆会”,专收失传家谱、残破账本、坟前碑文,甚至口述往事,整理成册。而这群孩子,便是其中最小的一支。
他看着他们红扑扑的脸蛋,忽然觉得胸口一热。
“好。”他点点头,“我听。”
孩子们围坐在石前,轮流朗读。有的结巴,有的跑调,但每一个字都念得认真。他们读到某个姓氏已在官籍中消失百年,读到一位女子因战乱被迫改嫁七次仍不忘原名,读到一名老兵临终前反复叮嘱孙子:“告诉世人,我们没逃,是我们全营战到了最后一人。”
随着诵读声起,空中光影愈发明亮。那些漂浮的名字开始旋转,形成一圈缓缓上升的光环,如同千灯书院的昭树之灯,升入苍穹。
柳知言闭上眼,泪水滑落。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这是新的开始。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残简堂内,裴砚正伏案誊写一部新发现的手札。这是一本被塞进墙缝的妇人日记,记录了三十年前一场大旱中的饥民互助。字迹歪斜,夹杂错别字,却真实得令人窒息。
他一边抄,一边低声念出声来。
忽然,窗外紫花飘入,落在纸上。他抬头望去,见庭院中站着一个小男孩,约莫七八岁,手中握着半截玉簪模样的木雕。
“你是谁?”裴砚问。
男孩不答,只将木雕轻轻放在门槛上,转身离去。
裴砚起身追出,却发现院中空无一人,唯有风拂动满园紫花,似有铃声隐约可闻。
他拾起木雕,翻转一看,背面刻着两个小字:
**归途**。
他愣住。
手指抚过那二字,仿佛触到了某种久远的温度。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清晨,他写下“芜归”时的心境??不是思念,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笃定:她从未真正离开。
如今,这木雕出现,像是一句回应。
他回到案前,提笔在日记末尾添了一句批注:
>“此非孤证,乃众声之始。凡百姓所记,皆为史也。”
然后合上册子,吹熄油灯。
月光洒进来,照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画??是小满多年前所绘:阿芜立于山巅,手持铜铃,身后万灯升空。画角题诗一行:
>魂散千江月,名存万家灯。
与此同时,西域某座荒废驿站里,黑袍女子再次翻开那本金边书籍。书页自动流转,停在全新一页。上面浮现的文字并非固定,而是不断变化,仿佛由无数细小的名字汇成:
>今日,河北赵氏族谱重修,补录女性十三人。
>今日,江南学子集资刊印《平民列传》,收录贩夫走卒事迹二百零七则。
>今日,宫中太子私习《民忆录》,遭太傅训斥,拒不销毁。
>今日,东海渔民打捞出沉船残板,上有“永昌三年,戍边将士合葬于此”字样,已报官立碑。
她静静读完,嘴角微扬。
“她选了人间。”她轻声说,“而人间,终于学会了记住。”
她合上书,推门而出。夜色深沉,沙漠寂静。但她知道,就在不远处的绿洲村落中,有一位盲眼老妪正在教孙女背诵一首童谣:
>“紫花开,铃声响,阿芜姐姐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