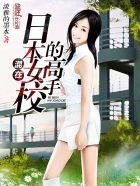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结局完整版 > 第1171章 如何才能不恨(第3页)
第1171章 如何才能不恨(第3页)
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神却清明如初。小满带着孩子们轮流守在他身边,每日为他朗读新收录的记忆。
“先生,河北赵氏族谱补录了您祖父的名字!”
“先生,江南有座桥以您命名了,叫‘知言桥’!”
“先生,有人说您才是真正的《民忆录》作者!”
柳知言只是微笑,不置可否。
直到某一晚,月色如霜,他忽然睁开眼,望向窗外。
“来了。”他轻声道。
众人回头,只见屋外并无一人,唯有风穿过竹林,送来一阵清脆铃响。
柳知言缓缓抬起枯瘦的手,指向远方。
“阿芜……在等我。”
话音刚落,天地忽静。
远处山巅,一朵紫花腾空而起,化作流光直冲云霄。紧接着,九州各地同时出现异象:
长安城上空浮现万千文字,如星雨坠落;
南方渔村的海面升起一圈圈光纹,似古老符印;
西北戈壁的沙丘自动排列成巨大铭文??“**记得**”;
就连深宫之中,铜镜也映出陌生女子的身影,手持铃铛,微微一笑。
柳知言闭上眼,嘴角含笑。
“我走了。”他说,“但我记得每一个人。”
气息断绝那一刻,他怀中的最后一枚忆种悄然碎裂,化作金粉四散。粉末随风而去,落入江河湖海,渗进田地山林。
十年后,有人在东海捕鱼时捞起一颗晶莹如泪的珠子,剖开一看,内部竟蜷缩着微型文字,密密麻麻,全是人名。
经考证,那是柳知言一生铭记的所有名字??三百二十七个被他唤醒的记忆主人,四百一十九段重见天日的湮灭之忆,连同阿芜、裴宛、小满、裴砚、黑袍女子、盲眼老妪、牧羊少年……乃至每一个曾说出“我记得”的普通人。
这颗珠子被供奉于共忆馆中央,命名为“忆心珠”。
每逢“全民共忆日”,珠子便会发光发热,投影出一段段记忆影像。人们围着它诵读、哭泣、拥抱、起誓。
而最令人震撼的是,每当有人真心说出“我记得你”,珠中就会多出一个名字,仿佛记忆本身正在繁衍。
小满活到了九十九岁,临终前仍在教孩子们写字。
她最后写下的字是:“**记**”。
学生们哭着将她的遗体安葬在千灯书院后山,与柳知言相邻。墓碑无名,唯有一幅画嵌于石中:少女持铃立于山巅,身后万家灯火升腾如星河。
画角题诗依旧:
>魂散千江月,名存万家灯。
多年后,一位考古学家在挖掘一座废弃驿站时,发现墙缝中藏着一本金边书籍。书页空白,唯有触碰者心中所想,才会浮现文字。
他试着默念母亲的名字,书中立刻显出一段记录:
>李氏春兰,生于启忆五年,育二子,善织布,喜唱童谣《紫花开》。临终前嘱咐:“告诉孩子们,要记得奶奶。”
他又念父亲,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