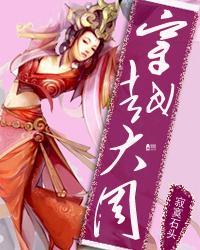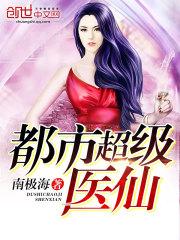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在哪看完结版 > 第1157章 灵门内的怪物(第2页)
第1157章 灵门内的怪物(第2页)
某个月圆之夜,井水忽然沸腾起来。蓝光冲天而起,映得整个山谷如同白昼。沈昭和小满冲出门外,只见井口缓缓升起一片焦黑的布条,上面赫然写着一行清晰的小字:
>“吴明远,生于癸亥年冬月十七,卒于甲子年四月初八。著《春秋遗稿》三十六卷,毁于火刑台。其妻李氏投井,其子流放岭南,死于途中。今其名归矣。”
沈昭浑身一震。
吴明远!那个在忆昭识海中不断闪现的老儒,那个被火刑烧死却仍护住经卷的男人!他的名字,终于回来了!
小满颤抖着伸手去接那片布,却被一股无形之力托住,布条缓缓飘向空中,化作点点蓝光,散入夜风。紧接着,第二片、第三片接连浮出,每一片都写着一个名字,一段生平,一句遗言。
>“苏婉清,女,曾任教坊司乐师。因谱唱《亡国谣》,遭割舌,囚十年而亡。临终前以血书壁:‘音不可灭,忆不可断。’”
>“陈九郎,七岁,因在家诵读《前朝志》,被举报,与其母同日杖毙。邻里收尸时,见其手中紧握半页残纸,字迹稚嫩:‘妈妈,我想记住你。’”
>“赵元朗,史官。奉旨修史,私藏真本于井底陶罐。事发后自刎于书房,血溅《实录》扉页,仅留一字:‘真’。”
一夜之间,三百二十七个名字回归人间。
第二天清晨,消息如野火燎原,迅速传遍全国。人们奔走相告,有人按名字寻亲,有人建碑立祠,更有无数人家在门前挂起白灯笼,上书“忆”字,以此纪念那些曾被抹去的存在。
与此同时,一种奇异的现象开始出现。
许多原本毫无关联的人,突然梦见相同的场景:一口古井,一场蓝雨,两名女子并肩走向铜镜,背影渐淡如烟。梦醒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竟能脱口说出某个陌生名字,或是哼出一首从未听过的古老歌谣。
医学堂称之为“集体还忆症”,佛寺则说是“亡魂托梦”,唯有民间百姓明白??这是忘川之门开启后的回响,是亿万被压抑的记忆洪流,终于找到了出口。
三年后的清明,沈昭带着小满登上皇城最高处的观星台。
这里曾是净魂司监察能俯瞰全城的地方,如今已被改建为“记忆阁”,专门收录各地送来的回忆文书。台中央立着一座青铜碑,正面刻着八个大字:
**“三令归一,魂归故里。”**
背面,则是一首短诗,据说是某位盲眼诗人梦中所得,醒来即吟,一字未改:
>雨落南陵井,
>风起旧宫门。
>一人分三影,
>双命换千春。
>火焚言不尽,
>刀斩忆犹存。
>若问归何处,
>人间处处痕。
小满仰头读完,忽然问道:“沈叔,如果那天忆昭姐姐没去见她……会怎样?”
沈昭望着远方起伏的城郭,良久才答:“世界会继续遗忘。人们会活得更轻松,更顺从,更麻木。他们会忘记母亲的容貌,忘记朋友的誓言,忘记战争的惨烈,也忘记爱的温度。到最后,所有人都变成行尸走肉,说着一样的话,做着一样的事,连梦都是统一的。”
他低头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但她去了。她选择了痛苦,选择了记得。因为她知道,真正的安宁,不是来自遗忘,而是来自面对。”
小满点点头,忽然跑开几步,从怀里掏出一支新削的炭笔,在石阶上用力写下三个字:
**“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