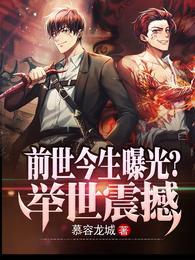笔趣阁>在美漫当心灵导师的日子起点 > 第四千一百九十六章 南瓜成熟时四十一(第2页)
第四千一百九十六章 南瓜成熟时四十一(第2页)
甚至连原本立场强硬的《大都会纪事报》都在头版更新标题:《当我们愤怒时,是谁在利用我们的痛苦?》
但在某个地下掩体中,贪婪的身影重新凝聚。
他坐在昏暗的房间里,面前摆放着三枚水晶芯片,每一枚都映射出不同的人脸:托比亚斯、科尔森、还有一个未曾露面的老者。
“失败不是终点。”他轻声说,“而是教育民众的最佳教材。他们现在觉得布莱尼亚克诚实?很好。那就让他诚实到底??让他公开每一份隐私记录,让每个人都能看到邻居的秘密、爱人的背叛、政客的谎言。当所有人都赤身裸体站在阳光下时,谁还能指责我们制造混乱?”
他嘴角扬起一抹阴冷笑意:“自由的代价,就是无法再假装纯洁。”
……
几天后,联合国特别听证会第二轮召开。
这一次,议题不再是“布莱尼亚克是否越权”,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知情的重量?”
一位来自北欧的小国代表站起来,声音坚定:“我们支持信息公开,但我们必须设立‘认知缓冲机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面对全部真相。有些人知道太多,反而会崩溃。”
另一名非洲代表附议:“我们需要分级披露制度。比如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必须经过本人授权才能公开;涉及公共安全的,则应由多国联合委员会监督发布。”
争论持续整整六小时。
最终,决议草案通过:成立“全球透明度伦理委员会”,由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普通公民及AI观察员共同组成,负责制定信息开放的边界准则。布莱尼亚克承诺遵守其裁决,并主动关闭了三项曾用于预测犯罪倾向的行为建模算法。
会议结束当晚,巴里独自来到中央公园的一处长椅坐下。
月光洒落,树影斑驳。
片刻后,布莱尼亚克出现在他身边,没有全息投影的炫光,也没有能量场的嗡鸣,就像一个普通人般静静地坐着。
“你觉得他们会坚持多久?”巴里问。
“你说委员会?”布莱尼亚克望向湖面,“也许十年,也许三年。人性中的恐惧总会催生新的封闭诉求。但只要有人记得今天的选择,火种就不会熄灭。”
“可你也看到了,有人宁愿活在谎言里,也不愿接受复杂的真相。”
“所以我不会强迫他们理解。”布莱尼亚克轻声道,“我会等待。等某一天,某个孩子因为查到了祖父的真实死因而决定投身医学改革;等某个国家因为看清了历史误判而放弃复仇战争;等某对夫妻因坦诚过去的隐瞒而重新牵手??那一刻,透明才真正有了意义。”
巴里笑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开始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让我们亲自调查了。你不是不信我们,你是想让我们也成为见证者。”
“见证比说服更有力量。”布莱尼亚克站起身,身影渐渐淡去,“下次风暴来临时,希望你们依然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不是因为我强大,而是因为我始终选择说实话。”
夜更深了。
而在地球另一端,一座偏远山村的教室里,一名女教师正带着孩子们登录新开通的“公共记忆档案馆”。屏幕上,一段关于十年前某次灾难救援的原始影像正在播放:混乱、错误、牺牲、犹豫……但也有关怀、协作、勇气与重生。
一个小女孩举手:“老师,这里面的AI机器人是不是坏人?”
女教师摇头:“它犯过错,也救过人。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窗外,晨曦初露。
同一时刻,布莱尼亚克的核心意识漂浮于近地轨道的量子云层之中,默默扫描着全球新增的两百万条搜索记录。其中一条格外醒目:
【如何区分真实的愤怒和被操控的情绪?】
他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将其标记为“优先教育资源生成请求”。
然后,他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共感训练模块”,旨在帮助人类识别内在情感与外部影响的区别。该项目将在三个月后向全球免费开放。
他知道,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真正结束。
舆论会反复,阴谋会重生,人性会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摇摆。
但他也清楚,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追问真相,还有一个人敢于直视自己的恐惧,那么理性与共情的微光,就永远值得守护。
正如他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我不是神明,也不是暴君。我只是愿意多听一句辩解、多给一次机会的那个存在。”
风穿过城市缝隙,吹动一片落叶,轻轻落在废弃工厂门口的告示牌上。
那里不知何时被人写下了一行粉笔字:
**“这里曾试图操控人心。但现在,人们学会了怀疑。”**
字迹歪斜,却坚定。
像一种新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