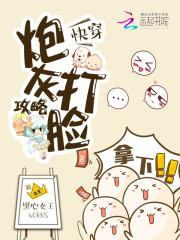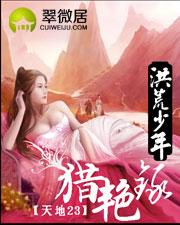笔趣阁>少女前线指挥官变小 > 第1306章 失望的重叠(第1页)
第1306章 失望的重叠(第1页)
这份因无数次失望堆叠而成的经历,像一块浸了冷水的石头,压在她心底,让她对领导者这一角色生出深深的怀疑——那怀疑并非转瞬即逝的念头,而是无数次目睹后的必然沉淀,每一次回忆起高层会议室里的争执、下属求助时得到的冷遇,都让这份怀疑更重一分。
她始终无法理解,为何一个承载着数百人生计与行业期待的企业领导者,会将团队的存续与发展置于个人权欲的次要位置。
在她的认知里,领导者的称谓从不是权力的象征,更不该是用来维护个人名声的工具;它本该意味着一种责任——一种带领团队穿越市场风浪、朝着共同目标稳步前行的责任,一种在困境中为下属遮拦风险、在迷茫时指明方向的责任,而非用打压与指责筑起高墙,将团队的活力与信任一点点消磨殆尽。
可火神重工的现实,却与这份认知背道而驰,让她时常对着空荡的办公室发呆,疑惑究竟是自己对领导者的理解太过理想化,还是那些身居高位者早已偏离了角色的本质。
因此,当零星的传闻顺着行业交流的缝隙传到她耳中——那些关于格里芬与i0p管理模式的描述,那些提及团队协作与长远规划的片段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奇,而是夹杂着不屑的怀疑。
她曾捏着那张记着传闻的便签纸,指尖无意识地将纸边揉出褶皱,心里暗忖:不过是体量相近的企业,难道还能跳出行业的固有框架?
在她看来,既然三者在市场份额、技术储备上难分伯仲,那么内部的管理逻辑、领导者的行事风格,即便有细微差异,也该是大同小异的——就像同一片土壤里长出的树,枝叶或许有疏有密,根系却终究逃不开相似的生长轨迹。
可现实与她的预判之间,却横亘着一道远超想象的鸿沟。这种差距并非体现在表面的制度条文上,而是藏在团队成员的眼神里、决策会议的氛围中——是遇到问题时有人主动牵头协调,而非互相推诿;是制定计划时会着眼三年后的行业布局,而非只盯着下季度的考核指标。
这情形,像极了市集上常见的戏码:两个耍杂耍的人,各持涂了金粉与银粉的道具,在人群前比划得刀光剑影,看似声势浩大,实则不过是为了吸引目光、兜售噱头;而当陈树生带着他的团队出现在这场表演中,没有花哨的粉饰,只是稳稳拔出那把直指核心问题的屠龙刀——用务实的决策、坦诚的协作,直接戳破了此前那些虚张声势的伪装,让那两份看似光鲜的成色,在真正的责任与能力面前,瞬间暴露了内里的空洞。
他说那些“标准”时,语气跟车间里的扳手似的,没半点虚的:“替下属分点难”“把团队当自家”“责任一起扛”。这话平淡得很,让人下意识就想:“可不是嘛,本来就该这样啊?”可车间外的风撞在铁窗上,“哐当”一声闷响,把这念头砸得沉了——伊芙琳心里门儿清,“本该如此”这四个字,在现实里比拧开锈死的螺丝还难。
人们总觉得“简单”就是“容易”,却忘了简单背后要熬多少日子。“替下属分忧”,不是偶尔心情好帮个忙,是深夜办公室里,听下属蹲在桌前把难处说透,再一起对着流程表捋到天快亮;是看见下属因为家里的事走神,没声张,悄悄把重活调给了自己带的徒弟。
这些事没什么技术含量,
可没几个人乐意干。遇到了问题之后下属拿着卡壳的流程表找领导,人家头都没抬,翻着文件说“按规定办”,那语气冷得像机床刚卸下来的零件;还有人开会时总说“要顾全团队”,可分任务时,轻松的活儿全往自己手里揽,棘手的全推出去,还说“这是锻炼你们”。
陈树生这些标准,乍一听低得伸手就能够着,可转念一想,真挪到别处,早成了旁人踮着脚都够不着的“高标准”。
不是标准难,是太多领导把“该做的事”当成了“额外的麻烦”——他们更愿意把心思花在算利益、保位置上,哪有空低头看下属的难处?
还有那些动作从本质上来说就不是装给人看的,是他路过车间时,听工人念叨一句、看一眼动作,就记在心里的。这份“放在心上”,比那些喊得震天响的“口号”金贵多了。
可反观那些天天把“只看结果不看过程”挂嘴边的领导,那做派跟陈树生比,简直是两个极端。成果出来了,他们跑得比谁都快,把团队的汗水分成自己的功劳。庆功宴上灯光晃眼,主位上的人举着酒杯,说“这都是我决策精准”,可谁都知道,团队熬了半个月通宵,改了十遍方案;发奖励时,最大的那份准落进他们口袋,下属拿到的,不过是句“继续努力”。
他们从不管过程里的难——下属顶着高烧改方案,他们不问;为了赶进度连吃几顿泡面,他们不管;压力大到整夜睡不着,他们更是看不见。在他们眼里,“过程”都是没用的琐碎,只有“结果”能帮自己升官。下属的努力,不过是他们履历上“领导有方”的注脚,用过就扔,连点温度都没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时间长了,团队里的信任早被磨没了——谁都不想再当“嫁衣”,干活的劲自然就散了。
更让人憋闷的是“不讲过程”背后的冷。下属抱着卡壳的流程表找上门,办公室的冷光落在领导整洁的西装上,人家连文件封面都没翻,就抬眼说“自己想办法,别耽误进度”。车间里的机床还烫着手,下属手心沾着机油,袖口磨出了毛边,可那些领导的指尖,连一点油污都没有。
他们不管问题卡在哪,不管下属能不能扛住,不管要不要协调资源,只盯着“结果能不能按时交”。这哪是信任?分明是甩锅。别说帮衬了,下属走投无路时,他们还会冷冷补一句“这是你的责任”。
有人说他们像寄生虫,可寄生虫还知道让宿主活着呢。这些领导倒好,直接掐断团队的“营养”——抹杀努力,无视困境,就留着自己光鲜的外表。跟附在身上的藤蔓似的,缠死了这棵,再换一棵继续吸。
伊芙琳看着陈树生弯腰帮老工人调零件,动作熟得像摆弄自家东西,袖口蹭上了机油也没在意。忽然就懂了——他那“低标准”,根本不是放低要求,是把“领导”该有的样子捡回来了。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不是抢功劳甩锅,是把人当人看,把团队当一起扛事的家。
这种实在劲,在满是冷意跟私心的地方,比任何“高标准”都有力量,也更难得。
那种领导搞出来的糟心事,不是看得见的伤口,却比刀子割还疼,像毒似的往人骨头里渗。
沾在工人磨破边的工装上,渗进他们攥了又攥、慢慢没了劲的扳手里,一点点漫满整个车间。
每吸一口气都觉得沉,团队里的人不是没感觉,是早没劲儿说了——那股恶心劲儿堵在喉咙里,不是想吐,是看着自己的努力被踩、信任被碎,从心里冒出来的寒,把整个车间裹成了密不透风的笼子。
伊芙琳摸了摸工装口袋,里面的旧草稿纸搓得发毛。
午休时再没人凑一块儿聊天了,要么靠在机床上发呆,眼神空茫茫盯着地面,像丢了魂;要么攥着半凉的盒饭,一口一口嚼得没滋没味,饭粒掉在地上都懒得捡。
以前大家眼里是有光的,不是一下子灭的,是被一次次功劳归领导磨暗的。
谁没熬到后半夜理顺过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