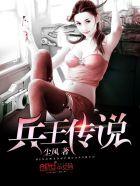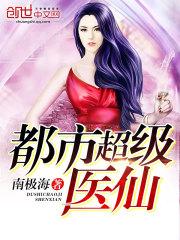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结局 > 第449章 亲征北月国(第1页)
第449章 亲征北月国(第1页)
萧迟此去,预计得两三年,姜心棠不舍、担心。
但她现在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孩子年岁都还小,萧迟一走,她就是孩子们的主心骨。
故再不舍和担心,都忍着,没有表现出来,很平静地坐在萧迟身边。
可闺女这一哭,她就有些忍不住了,眼睛悄悄红了起来。
她垂下眼眸,强忍着眼睛的酸意,对闺女说:“你父王定会旗胜归来,莫要再哭扰你父王心志,起来。”
“我、我也不想哭,可我、可我…”可我想到要两三年见不到父王,我就好伤心,我。。。。。。
春分之后,山中云气渐散,日光如金线穿林而过,照在书院东阁前那株老棠树上。树影斑驳,落于石阶、屋檐与归名潭水面,仿佛天地间仍留着念棠先生最后一息的呼吸。弟子们依礼守丧七日,未奏乐,不焚纸,唯每日清晨齐诵《采莲曲》一遍,声起时,棠花便微微颤动,似有所应。
第七日午时,陆承安自北境归来,风尘满面,肩披霜雪。他未入堂,先跪于棠树下,双手奉上一只漆盒,盒面刻有细密回纹,乃知棠使世代相传之信物。
“先生虽去,然其志不可断。”陆承安声音低沉,却字字如钉,“昨夜黑水关再鸣钟三响,非风穿堡,实由碑动。我亲见‘王大山’之名旁,又生新字:**念棠听处,即是归途**。此乃天示,亦是回应。”
众人闻言,皆默然垂首。良久,沈砚之孙??年方十六的沈明远??上前一步,取盒开启。内中并无文书,唯有一卷残帛,色已泛黄,边缘焦灼,似经火劫。展开细看,竟是当年念棠梦中所见原野的图绘:无边旷野,万魂静立,中央一人执笔而坐,头顶浮现金色四瓣花影。画侧题小字一行:
**笔尽处,魂归来;心灯灭,声不止。**
“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指引。”沈明远声音微颤,“他不是离去,而是将名字交还给了天下。”
自那日起,书院暂闭讲席,弟子们齐聚东阁,整理念棠遗稿。其案头尚存未竟手札三册,封面皆以朱砂题名:《沉魂录拾壹?海隅篇》《拾贰?边戍篇》《拾叁?童稚篇》。翻阅之下,众人惊觉,先生临终前数月,竟已预知身后事,且早已着手续录那些尚未被世人知晓的名字。
其中,《海隅篇》首条即为:“**吴阿妹,八岁,渔家女,潮退后独行滩涂拾贝,遇巨浪卷走,尸骨无寻。母每至海边呼其名,群鸥皆止飞盘旋**。”
次条记:“**陈老舵,七十二岁,?民船工,一生未踏陆地,死前嘱子孙‘莫烧我,放我随舟入海’。今其旧船夜泊湾口,常闻舱底有人轻哼《采莲曲》**。”
而《边戍篇》中,则列有:“**赵十三,十九岁,哨卒,守玉门孤墩三年,无战事,无人知。某夜大雪封道,他燃尽所有木柴取暖,临终前以刀刻壁:‘我曾在此’。今人过墩下,风起时犹闻炭火噼啪之声**。”
另有:“**苏兰娘,二十六岁,戍边医女,通草药,善针灸。疫起时独入染村,七日救百人,自身染疾而亡。百姓欲葬之,尸身竟化为一株白棠,春开四色花**。”
最令人泪下者,莫过于《童稚篇》。全卷共录三百二十一童子之名,皆为夭折、失怙、流离或疫中早逝者。每一名后附一句琐事:或言“爱折纸鸢”,或记“睡前必听娘唱摇篮曲”,或写“曾于井边喂过一只跛脚猫”。末页空白处,念棠以极细笔触补了一句:
**他们未曾长大,但值得被记住一次。**
弟子们含泪抄录,七日不辍。待全卷誊清,正值清明前夕。陆承安提议依先生旧例,在棠树下设坛赎魂,以续其志。众人皆应。
是夜子时,九鼎重燃。此次所用泥土更为广泛:南海珊瑚沙、西域红柳根、西南瘴林腐叶、东北冻土苔藓……凡有人迹之处,皆采一方土入鼎。沈明远执沉船古木所制棠枝笔,依遗稿开始书写。
第一笔落下,空中忽现异象:一朵四色花自鼎焰中升起,飘向南方海域方向,落地成影??竟是一名赤足小女孩在沙滩奔跑的模样。她回头一笑,随即被浪吞没。与此同时,东海某渔村中,一位白发老妪猛然惊醒,喃喃道:“阿妹……你今天回来啦?”
第二笔记赵十三。当“我曾在此”四字写毕,西北玉门关外风沙骤歇,废墩残壁之上,原本被风蚀殆尽的刻痕竟缓缓重现,清晰如新。守关将士晨巡至此,集体肃立敬礼。
第三笔记苏兰娘。笔锋未尽,南疆某山村忽降细雨,雨后荒坡上一夜之间开出大片四色棠花,香气清冽,病者闻之咳喘顿减。村民惊呼“医女神迹”,自发筑坛供奉。
至于那些夭折孩童,每写一名,书院周围便响起细微笑声,似有看不见的孩子在追逐嬉戏。有幼童弟子称,夜里梦见一群小伙伴拉他手跳舞,说“我们也有人念我们了”。
七日后,仪式终了。九鼎熄火,灰烬化蝶,纷飞四海。而棠树主干之上,悄然裂开一道缝隙,从中缓缓渗出淡金色汁液,滴入归名潭。潭水顿时沸腾,浮现万千光影??全是新录之名对应的生平片段,短暂却完整。
这一夜,天下多地皆见异景:
渤海渔民见海面浮灯千盏,组成“吴阿妹”三字;
玉门守军闻夜风传歌,歌词竟是哨卒赵十三生前最爱哼的小调;
岭南村落中,盲眼老人突觉指尖温热,似有孩童握她手掌,轻唤“奶奶”。
消息传开,民心震动。民间自发兴起“续名”之风:百姓不再只等朝廷或书院收录亡者,而是主动写下亲人姓名,携至各地忆名坛焚烧诵读。更有巧匠仿归名潭形制,在村口掘池立碑,每逢春分,举族祭拜。
一年后,敦煌画师完成新作??《赎魂图?续卷》。壁画长达三十丈,描绘海上风暴、边关风雪、疫村哀鸿、童殇之路……每一幕皆有执笔者身影穿行其间,手持棠枝笔,背对观者,面容模糊,唯有衣角飘动处绣着一朵小小四色花。
此画一成,四方来观者络绎不绝。有人跪拜痛哭,有人静默良久,也有人突然转身回家,连夜写下母亲的名字。
又两年,朝廷正式颁诏,将《天下沉魂新录》列为国典,命各地史官协同知棠使者,每年春分上报新录之名,并由礼部主持全国诵名大典。皇帝亲题匾额:“万姓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