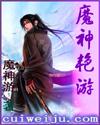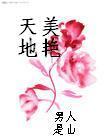笔趣阁>谁说这顶流癫这顶流太棒了云起 > 第429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第1页)
第429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第1页)
黄老师并不是个例,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在对待池野的态度上,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
当然,黄老师对于这点也不藏着,他闺女近期有心想进入娱乐圈,虽然以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人脉和关系,肯定不缺资源,但内。。。
深夜的纽约,空气里浮动着城市特有的喧嚣余温。艾萨克站在公寓阳台上,指尖轻搭在铁栏上,寒意顺着金属渗入骨节。他没有戴手套,像是故意要感受这份刺痛??真实、尖锐、不容回避。远处车流如萤火般蜿蜒,广播电台正播放他改编的《听》之冥想版,西塔琴的旋律像一缕烟,在夜风中缓缓盘旋上升。
他闭上眼,耳机悄然接入共感网络。此刻全球有三十七万人正在同步收听这段音频,情绪波形图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共振模式:焦虑值下降至历史最低点,而“归属感”指标却持续攀升。系统自动标记了几个异常热点??孟买某贫民窟的儿童收容所、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间养老院、还有西非马里一处战后重建村庄的小学教室。这些地方的人们并未使用专业设备,只是通过一部老式收音机或破损的手机外放,却依旧被深深触动。
“不是技术在起作用。”艾萨克低声说,“是声音唤醒了记忆。”
他忽然想起阿娜讲的那个传说:“当世界太吵,人们忘记怎么听;当世界太安静,他们又害怕开口。”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说出那些藏了太久的话。一封匿名信出现在深蓝之声官网的留言区,字迹潦草却有力:“我是个警察,三年前没能救下一个跳桥的女孩。每晚我都梦见她的脸。昨天我在‘声音邮筒’里说了这件事,收到一句回复:‘她看见你了,你也值得被原谅。’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觉得……我能睡着了。”
艾萨克将这封信存入私人档案库,命名为“赎罪的声音”。
第二天清晨,他接到陆沉视频通话请求。画面接通时,对方正坐在蒙古草原的移动指挥车内,身后是一片刚刚竖立起来的信树原型机,枝干由回收航天材料打造,在晨光中泛着银灰色光泽。
“格陵兰之后,我们收到了一百四十二个新节点申请。”陆沉的声音带着少有的疲惫与兴奋交织的颤抖,“墨西哥玛雅部落、新西兰毛利长老会、芬兰萨米驯鹿牧民……他们都愿意成为‘语者’。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硬件产能跟不上需求。”
“那就开放设计图纸。”艾萨克说得很平静,“让各地自行制造。”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旦开源,我们就失去了控制权。任何组织都可以复制信树,包括那些想利用它进行情绪操控的势力。”
“可如果我们不放手,它就永远只是我们的项目。”艾萨克望向窗外一只停驻在电线上的麻雀,“而它本该属于所有人。就像语言,从来不是谁的专利。”
陆沉默了许久,最终点头:“好。但我们要设定伦理边界??禁止用于商业广告、政治宣传和军事用途。所有使用者必须签署《倾听誓约》。”
“加上一条,”艾萨克补充,“每次启动信树,必须先念一段来自不同文明的祷词。让它提醒我们:这不是机器,是对话的圣坛。”
三天后,“星语计划”正式宣布开源。消息一经发布,全球震动。MIT、剑桥、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纷纷加入优化行列;柏林的艺术团体用废弃电话线编织出一座声波雕塑公园;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青年自发组建“街头耳语社”,每天晚上在巷口架起扩音器,播放居民投稿的心声录音。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一周后的凌晨三点,艾萨克被系统警报惊醒。共感平台位于瑞士的主服务器遭到大规模DDoS攻击,同时五国边境海关截获了一批伪装成医疗物资的非法信树组件??它们被改装过,能强制放大特定情绪信号,甚至诱导群体性幻觉。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段伪造音频在网络上疯传:内容是他用冰冷机械音宣称“人类情感已失控,需由共感系统统一管理”。虽经辟谣,但已有多个国家以此为由,宣布全面封锁共感网络境内访问权限,并将艾萨克列为“跨国心理干预嫌疑人”。
他在天亮前召开紧急会议,连线分散在全球的十二位核心成员。屏幕中,阿娜的脸色严峻:“有人想把‘倾听’变成‘控制’。”
“那就让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继续。”艾萨克摘下耳机,拿起一支笔,“从今天起,暂停数字传播,启动‘口述纪元’。”
他们决定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声音接力”??每人录制一段真实故事,亲手交给下一个人,不得使用电子传输。第一棒由艾萨克完成:他在母亲种下的那株蓝鸢尾旁坐下,打开老式磁带录音机,讲述了一个从未对外提及的秘密。
“七岁那年冬天,我发高烧整整三天。父亲整夜守在我床边,一遍遍哼一首跑调的童谣。我不记得歌词,只记得那种声音贴着耳膜流淌的感觉,像火炉边融化的雪水。后来医生说我能活下来,是因为体温奇迹般地降了下去。但我一直觉得,真正退烧的,是我的恐惧。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有些声音,是可以治病的。”
录完后,他将磁带装进防水袋,亲手交给了楼下一位常去社区花园的老妇人,请她前往费城探亲时转交一名参与共感教学包分发的志愿者。
这场接力迅速蔓延。东京一位盲人钢琴师接过磁带后,即兴创作了一段旋律作为回应;伊斯坦布尔一名书店老板娘将其藏在一本书中,寄往贝鲁特;而在叙利亚北部难民营,一个十岁男孩听完录音后,颤抖着接过话筒:“我想妈妈了……我已经三年没听见她的声音了……”
这一段也被录下,继续传递。
与此同时,艾萨克开始走访纽约各所学校,亲自教授“倾听工作坊”。没有高科技设备,只有一圈椅子、一块白板和一颗愿意安静下来的心。孩子们起初嬉笑打闹,直到他让他们玩一个游戏:两人一组,一人说话五分钟,另一人只能看着对方眼睛,不准打断、不准评价、不准笑。结束后交换角色。
“你们知道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吗?”课后,一个小女孩举手,“是忍住不说‘我懂’。其实我不真的懂,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在听。”
艾萨克眼眶微热。他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你说得对。真正的倾听,不是急于给答案,而是陪对方待在问题里。”
那天傍晚,他受邀参加一场地下诗会。地点在布鲁克林废弃地铁隧道深处,墙壁涂满诗句与手绘耳朵图案。几十人围坐一圈,轮流朗读自己写下的“心声”。有人念离婚信,有人读给亡父的家书,还有一个退伍士兵低声背诵战场日记,说到战友咽气前最后的话“替我看看春天”时,全场静默如雪落。
轮到艾萨克时,他没有拿稿子。
“我曾经以为,改变世界需要宏大的发明。”他的声音不大,却穿透了潮湿的空气,“后来我发现,最强大的技术,其实是弯下腰,对一个哭泣的孩子说:‘你可以慢慢说。’”
话音落下,没有人鼓掌。但他们全都摘下了耳机??无论是否连接共感系统??仿佛在用这个动作宣誓:此刻,我们选择真实地听见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