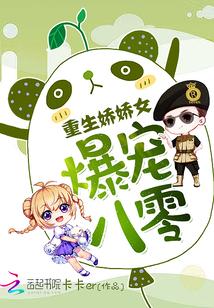笔趣阁>天可汗回忆录七星 > 第531章 这不都学的你么(第2页)
第531章 这不都学的你么(第2页)
笑谈之中,谣言自溃。土司见势不妙,斩二人首级献降。首级送至长安,沈怀礼命人悬于鼓台三日,不加羞辱,只立一牌:“此二人,才智足以治国,却用于毁国。惜哉。”
秋分那天,昆仑墟迎来第一场雪。张念独自登台,在“始问”碑旁新立一块石,上刻“常答”二字。他敲响小鼓,朗声提问:“我们还要问多久?”
山谷寂静,风卷雪花。
片刻后,远处村落传来回应鼓声,接着是另一处,又一处……七声响后,齐齐停歇。
张念微笑,自怀中取出一本册子,翻开朗读:“第一年,我们问税去了哪里;第五年,我们问官是否超支;如今第十一年,我们问??如何不让下一代再问同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长安太学举行首届“退场仪式”。沈怀礼宣布辞去共算总领之职,推荐李芸娘接任。全场肃立,无人鼓掌,唯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每位学子都在记录这一刻,如同记录一笔不容篡改的账。
临别那日,柳含烟送来一只新鼓,鼓面以雪蚕丝织就,轻薄如雾,却坚韧无比。她道:“听说昆仑山顶有种风,能穿透金石。我让人采了十年才织成这面鼓,专为传声千年。”
沈怀礼抚摸鼓面,忽觉眼眶发热。他想起南诏山村的第一笔账,想起柳含烟中毒时嘴角的血痕,想起张二狗儿子捧鼓而来时冻红的脸,想起李芸娘殿前那一句“她们为何想掌权”……
“也许有一天,”他轻声道,“人们不再需要我们了。”
柳含烟微笑:“那才是成功。”
他点点头,背起布囊,再次踏上西行之路。这一次,没有送行,没有仪仗,只有身后渐渐响起的鼓声,一声接一声,如心跳,如呼吸,如大地深处永不枯竭的回音。
行至玉门关外,暮色四合。他停下脚步,从囊中取出南诏山村的原始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提笔写下:
“正月十八,晴。风起于青萍之末,终成万里之啸。吾道不孤,后必有继。此身虽倦,心火长明。”
写毕,他将账本埋于关城之下,堆石为记。转身之际,忽见远方沙丘上,一点红影飘动??是个小女孩,手持木鼓,正向他跑来。
她气喘吁吁停下,仰头道:“爷爷说,您若经过,让我交给您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渠水清了,牛回来了。’”
沈怀礼怔住,良久,缓缓蹲下身,与她平视。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陈阿牛。”
他猛然记起??那是南诏山村第一个敢问他“我家牛死了怎么办”的老农,也是第一个学会记账的村民,十年前已病逝。
他闭上眼,仿佛看见那个佝偻的身影站在田埂上,牵着一头瘦牛,笑着说:“先生,我现在知道,牛死了,不是天要罚我,是有人克扣了防疫药钱。”
睁开眼,他摸出随身小鼓,递给女孩:“你会敲吗?”
“会!”她用力点头。
“那就替我敲一声。”
女孩接过鼓,举起小槌,狠狠一击??
咚!!
鼓声撞上玉门关墙,反弹向无垠大漠,惊起一群归鸟,振翅飞向血红夕阳。
沈怀礼望着那抹残阳,喃喃道:“地若回声,灵便活着。”
风起,雪落,驼铃悠悠。
而在千里之外的长安、扬州、陇右、交州,无数间议事坊中,灯火依旧明亮。
有人在核账,有人在记事,有人在教孩童写下一个字??“问”。
鼓架之上,一面面“常问”鼓静静伫立,等待下一双叩击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