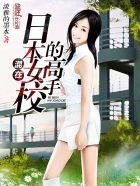笔趣阁>朕真的不务正业篱笆好文学 >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第2页)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第2页)
“陛下急令!”他喘息道,“西北三镇兵变,边军统帅陈武昭自立为王,打出‘清君侧,废苛政’旗号,已有五万将士响应!京畿戒严,百官入宫议事,请先生速赴太庙共商对策!”
满堂哗然。
有人惊呼:“信火教人质疑,如今竟酿成叛乱?!”
有人怒斥:“早该查封学堂,纵容妄言,终致天下大乱!”
更有昔日支持者面露犹豫:“难道……真是我们错了?”
阿禾却不动。
她缓缓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风雨交加的群山。良久,才转身问道:“陈武昭可是当年信火第一批旁听生?”
校尉一怔:“正是。他曾在此修习三年,后考入武备院,历任边军参将、总兵,战功赫赫。”
阿禾点头:“那他就不是反贼。”
众人愕然。
“他是病人。”她声音平静,“一个被体制折磨太久,终于忍无可忍的病人。他的刀指向朝廷,但他的问题,其实早就写在十年前的作业里??”
她从讲台抽屉取出一份泛黄卷宗,展开念道:
>“老师,如果法律只保护有权的人,那它还算法律吗?
>如果士兵流血戍边,家人却被官吏强征田产,这样的国家值得效忠吗?
>我们宣誓忠于皇帝,可谁能保证皇帝不会背叛我们?”
念毕,她抬头:“这不是煽动叛乱,这是绝望的求救。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派兵镇压,而是派人去问他:你想说什么?你需要什么?为什么非得起兵不可?”
校尉愣住:“可……可陛下召您是为定策平乱啊!”
“那就让我带一句话进宫。”阿禾取笔研墨,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大字:
>**先问缘由,再定罪名。**
她说:“告诉赵珩,真正的稳定,不是靠杀人封口,而是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说出不满。否则,今天杀了陈武昭,明天还会有李武昭、张武昭。只要问题还在,火种就不会灭。”
校尉领命而去。
雨势渐歇,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照入堂,落在那只铁盒上,照亮了《缄口录》三个字。
黄穗忽然开口:“老师,我想去西北。”
阿禾看着她:“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
“我知道。”她目光坚定,“但我母亲死于‘不该说的话’,我不想再让任何人因‘不敢说的话’而死。我要替她走完没走完的路??把问题送到权力耳边,哪怕要用脚丈量千里。”
阿禾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一枚铜铃残片,递给她:“这是谢秀奇先生遗物,当年他在狱中摇铃计时,十三秒一响,提醒自己不要睡去,不要忘记。你带着它,让它替你数着心跳,也数着信念。”
黄穗双手接过,郑重系于腰间。
当晚,阿禾独坐院中,翻阅旧日笔记。她翻开一页,上面写着赵珩少年时的一段对话:
>赵珩问:“若天下人都错,只有我对,我该怎么办?”
>阿禾答:“那你更要小心。因为你可能正站在最大的幻觉之中。”
她轻叹一声,提笔续写道:
>如今他已是明君,可明君也会犯错。
>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暴君横行,而是贤主自以为无所不能。
>当一个人坚信自己在行善,便最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