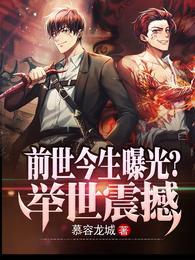笔趣阁>新风净化工程 > 第469章 ○奉天养老院之4(第3页)
第469章 ○奉天养老院之4(第3页)
“这树比我岁数都大,”郑德山摸着树干上的年轮,“当年我进厂时,它就这么粗,现在更壮实了。”赵大爷拄着拐杖来看,说:“它见证了机床厂的红火,也看着咱们养老院的热闹,是有福气的树。”
张桂兰大娘带着王姐给树浇水,用的是食堂的淘米水。“老周说过,树跟人一样,得用心疼,”她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旺。”李建国大爷则在树下摆了个小桌子,说以后就在这儿下棋,“让老槐树当裁判”。
老陈大爷每天都来树下站会儿,摸着树干,像在跟它说话。有天突然下大雨,他非要在树下守着,说“怕树淋着”。郑德山拉他进屋,说:“老伙计,树比你结实,淋不坏。”
雨停后,老槐树的叶子更绿了,水珠从叶尖滴落,像在点头。叶东虓看着它,突然觉得,养老院的故事,就藏在这年轮里,一圈是机床厂的红火,一圈是养老院的温暖,还有一圈,是正在继续的,平平淡淡的好日子。
第四十九章壁炉边的“新年歌”
除夕那天,养老院的壁炉烧得旺旺的,老人们围着壁炉守岁。王姐带着伙计们来帮忙,包了饺子,炸了麻叶,还买了烟花。
郑德山给王满堂的照片前摆了副碗筷,倒了杯酒:“老伙计,十年了,咱们的葡萄树都长大了,你在天上看着,该放心了。”赵大爷则给老叶的照片鞠了一躬:“当年没跟你说过,你修的机床,是全厂最好的,我佩服你。”
张桂兰大娘给每个人发了红包,里面是块杏仁糖:“老周说,新年吃块糖,一年都甜。”李建国大爷给老陈大爷剥了个橘子,说:“吃点酸的,醒醒酒。”老陈大爷嚼着橘子,突然说:“年……好……”大家都愣了,随即爆发出掌声。
小宇弹着吉他,和朵朵一起唱新年歌,老人们跟着哼,跑调跑得厉害,却比任何歌都动听。壁炉里的火“噼啪”响,像在伴奏,窗外的烟花在夜空绽放,照亮了老槐树的影子,也照亮了记忆角里的老物件。
郑德山举起酒杯,对着老伙计们的照片,对着壁炉,对着窗外的烟花,说:“新年好啊,咱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甜。”大家都举起杯,酒液里映着炉火,映着笑脸,映着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
第五十章葡萄架下的“时光信”
十年之约到了,老人们在葡萄树下挖时光胶囊。郑德山的手颤巍巍的,赵大爷在旁边指挥:“慢点挖,别碰着胶囊。”张桂兰大娘攥着银顶针,说:“不知道我的顶针还亮不亮。”
胶囊挖出来了,锈迹斑斑,却完好无损。打开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木头、布料和金属的味道涌出来,像十年前的时光,一下子扑到眼前。
郑德山摸着旧棋盘,上面还有王满堂偷偷挪棋子的痕迹;张桂兰大娘拿起银顶针,对着太阳照,还像当年一样亮;赵大爷的红木拐杖,包浆更厚了,握着更顺手;李建国大爷的食堂账本,纸页更脆了,却还能看清“白菜三分钱一斤”的字迹;老陈大爷的齿轮模型,轻轻一推,还能转。
小宇和朵朵也来了,看着这些老物件,听老人们讲十年前的故事。“这就是时光啊,”小宇感慨,“能让物件变老,却让故事变甜。”叶东虓把新的故事本放进胶囊,说:“再埋十年,让后来的人看看,咱们又攒了多少好日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重新埋好胶囊,老人们坐在葡萄架下,吃着今年的新葡萄,甜得眯起眼。郑德山看着葡萄藤,说:“老伙计们,下一个十年,咱们还在这儿聚,好不好?”风穿过葡萄叶,沙沙响,像在应和。
阳光正好,岁月安稳,奉天养老院的故事,还在继续,像这葡萄藤,一年年,爬满架,结满果,甜了一茬又一茬。
第五十一章齿轮与画笔的约定
老陈大爷的齿轮模型在时光胶囊里藏了十年,重新取出后,竟成了小宇的“修复课教材”。小宇如今是文物修复师,带着放大镜仔细清理模型上的锈迹,老陈大爷就坐在旁边看,手指跟着齿轮的纹路动。
“陈爷爷,您看这齿轮咬合的角度,当年的工匠多厉害,”小宇边擦边说,“我得把它修得跟新的一样,还能转。”老陈大爷突然抓住他的手,把模型放在他掌心,含糊地说:“传……你……”
郑德山在旁边笑:“老陈是把你当徒弟了。”张桂兰大娘给小宇缝了个工具袋,上面绣着齿轮图案:“拿着,修东西也得有个顺手的家什。”
模型修好那天,小宇给它装了新的马达,齿轮转得又快又稳。老陈大爷看着转动的齿轮,突然笑出声,像个孩子。小宇举起模型说:“陈爷爷,咱们约好,等我修复完机床厂的老设备,就把这模型放进去当展品,告诉大家这是您的宝贝。”老陈大爷用力点头,眼里的光像齿轮上的反光。
第五十二章缝纫机上的“青春记忆”
王姐的女儿要结婚了,张桂兰大娘坚持要给她做件嫁妆——件绣着龙凤呈祥的红盖头。“当年我结婚,盖头是老周的妈绣的,”大娘踩着缝纫机,“现在我绣给你,让福气传下去。”
王姐和女儿围在旁边看,大娘的手有些抖,针脚却依旧细密。“这凤凰的尾巴得用金线,”她教姑娘穿线,“老辈人说,金线能锁住福气。”郑德山凑过来看热闹:“这手艺,比当年给老周补袜子强多了。”
盖头绣成那天,红得像团火,龙凤仿佛要从布上飞出来。王姐的女儿捧着盖头,给大娘磕了个头:“张奶奶,这盖头是最好的嫁妆,我要传给我闺女。”大娘摸着姑娘的头,缝纫机“咔嗒”响了一声,像老周在旁边叹气——是欣慰的那种。
记忆角多了个新展柜,放着三代人的嫁妆:老周母亲的绣品、张桂兰的银顶针、王姐女儿的红盖头。叶东虓在展柜前写了行字:“针线缝补的,不只是衣裳,还有日子的传承。”
喜欢厂院新风请大家收藏:()厂院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