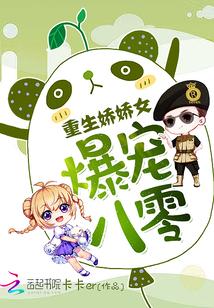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之扶摇河山结局 > 第六百零二章 策问勘世道(第3页)
第六百零二章 策问勘世道(第3页)
殿试为天子主考,而且只考较策问,过殿试者皆为天子门生。
每次会试上榜的举子,多达数百名之多,头名为会元,其后依次排名,以至于和乡试一样,也有孙山末尾的雅事。
但是,会试上榜的举子,即便榜上排名靠后,如有神鬼之笔的策问之才,一篇宏文得天子青睐,成败反转,同样也能金榜登高。
因此,但凡举子心怀青云之志,有独占鳌头之心,无不是精通策问之学。
贡院内三千余名应考举子,在经过了两场六日的考较,点灯熬油,绞尽脑汁,大多数人都已神思疲惫。
但是所有的举子,在前两场考较之中,不管是不尽人意,或者是志得意满。
没有人会有半点松懈,人人心中都牟足尽头,将剩余的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在第三场策问比试。
大周会试策问之比,和前程规制大同小异,也是出题策问五论。
但是与前朝相比,也有所不同,主要出于务事而论,致事求深。
因此,会试三场五道策问题,首题为主题,其余四题以首题为干,延展出题而问。
上届春闱的策问制题,便是从首题派生出海政、河防、边事、征赋等四小题
也就是说,策问首题是重中之重。
如果首题答问写得不成体统,糟糕坏事,其余四题就失去根源,三场策问就会一败涂地。
策问之学,比起严谨规整的书经八股,似乎显得更加挥洒,但是精深策问之学,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贾琮自从拜柳静庵为师,每年柳静庵都会给他列大量书目,涉及诸事百家,让他开阔视野,夯实策论根基。
其中磨砺积累,数年辛劳为一日,滴水穿石始成功,想要科场上先人一步,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
等到三通鼓声停歇,贾琮磨墨沾笔,只见两名举着考牌的差役,在场走入舍巷。
所有考生目光灼灼,全部汇集到考牌上的策问首题:
学人皓首穷经,治学深思,终为俯之以王事,上古皇帝之始,即为不易之圣贤道统。
然春秋有变迁,君王有贤愚,黎民分贫富,敌酋有多寡,臣僚各忠奸。
圣贤道统不可易,然一时之法,无一定之论,何以可治百世之事?
先贤有云: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融天下之心。
盖以本源治道之基,众法归一,使普天率土,士民黎庶,悉共于理义。
无本末忤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何以致之?
……
贾琮全神贯注浏览考牌上的考题,并飞快的执笔记录,但读完首题内容,心中微微一动,若有所思。
在贾琮所在号舍之前十几个位置,正是杭州府解元林兆和的号舍。
当差役的考牌游走到号舍之前,他全神贯注看过首题,并飞快笔录下来。
等到录完其他四道策问题,林兆和又回到策问首题仔细阅读。
等到他读完题意,微微一揣摩,心中生出古怪,眉头微微锁起……
随着差役举着考牌在舍巷中走动,越来越多的举子看清了首题,许多人的脸上都显出难色。
不得不承认策问首题,题意宏大,思虑深远,但越是这样的题目,举子策问答题,掌控的难度就越大。
已经有不少举子心中暗骂,这策问首题雄奇怪丽,汪洋恣肆,气势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