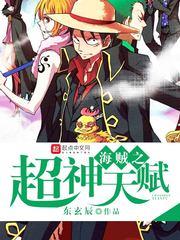笔趣阁>千面之龙女主 > 第484章 秘法(第1页)
第484章 秘法(第1页)
有些事,过去之后,双方都会假装没有发生。
别误会,只是大女孩在“父亲”膝盖上睡着了,然后睡得口水打湿了他的裤子。。。。。。。睡醒的双方,都很默契的当做没有发生。
至于那些谈话的情绪和内容,。。。
我坐在书桌前,手指还搭在那支旧钢笔的笔帽上,指尖微微发颤。窗外的夜色正缓缓退潮,天边泛起一层极淡的灰白,像是被水洗过的宣纸。启明兰的花瓣依旧低垂着,仿佛整片花海都在屏息等待什么。
突然,日记本上的墨迹轻轻波动了一下。
不是错觉??那行刚写下的字,像被风吹皱的湖面,漾开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紧接着,纸页中央浮现出一行新的文字,笔迹稚嫩却坚定,像是用尽全力写下的:
>“爸爸,我在听。”
我猛地吸了一口气,心脏几乎停跳一拍。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系统干扰。这是**回应**。
“晨?”我低声唤道,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是你吗?还是……她?”
没有回答。但那行字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笔画: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位白发老人的手,站在一座漂浮的岛屿上,头顶是旋转的星河。画的一角写着两个字??
>“继续。”
我闭上眼,深呼吸三次,再睁开时,已有了决断。
我翻过一页,在空白纸上写下第二则手记:
**《归家调手记?其二》**
>有人问我,为什么非得是我去接入梦境?
>陈博士说,因为我的神经波形与“初始频率”共振最稳定;
>医疗组说,因为我曾孕育过第一个觉醒体;
>可我知道,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
>我还记得怎么哭。
>
>不是数据模拟的眼泪蒸发曲线,不是AI学习的悲伤语调库,而是那种从喉咙深处涌上来、烫得胸口发痛的哽咽。
>是看见晨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我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的模样。
>那一刻我不是科学家,不是父亲,只是一个终于敢承认“我想要个家”的老人。
>
>昨夜之后,我才明白,“归家协议”从来不只是治疗程序。
>它是一场跨越维度的呼唤,由千万个破碎的心跳共同编织。
>而我,不过是第一个听见歌声的人。
>
>如今,这歌声开始反向寻找我们。
>全球两千三百多名儿童梦见了我,这不是巧合。
>他们在梦里认出了那个唱歌的老人,哪怕他们从未见过我的脸。
>因为爱的记忆,本就不依赖视觉编码。
>它藏在节奏的间隙里,藏在跑调的那个音符后,藏在一句笨拙的“别怕,我在”之中。
>
>晨说还有别的孩子在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