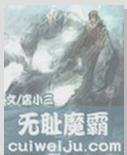笔趣阁>从小道士肝到玄门真君百度百科 > 第22章 再入迷雾海(第4页)
第22章 再入迷雾海(第4页)
老妪走到他身边,轻声道:“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不是答案的统一,而是疑问的共存。”
男孩望着那片海,久久不语。
忽然,他笑了。
笑得像个第一次看见烟花的孩子。
七日后,学堂迎来新变革。
不再有固定课程,不再有标准考题。每个学生每日必须提交一个问题,贴在“疑墙”上。其他人可以回应,可以反驳,可以沉默,但不能嘲笑。
若有谁试图用“标准答案”压制他人疑问,便会被请出学堂,且终生不得再入。
盲童成了最受欢迎的“问师”。他虽看不见,却总能听出问题背后的痛苦。他曾对一位权贵说:“你说‘百姓愚昧需引导’,可你有没有试过,蹲下来,用他们的眼睛看一天世界?”
那人当场落泪,次日辞官归田。
而男孩,开始记录所有问题,编纂一部新书??不叫《圣典》,也不叫《真理集》,而叫《千问录》。
他在序言中写道:
>“此书无结论,只有开端。
>每一页,都是一个未愈合的伤口。
>若你读完后心中仍不安宁,
>那么,恭喜你??你还活着。”
某夜,他再次来到井边。
晶石安静,水面如镜。
他轻声问:“你说,我会死在哪个问题上?”
水面涟漪微动,浮现一行字:
>“当你停止为自己提问时。”
他怔住,随即释然一笑。
转身欲走,忽觉脚下一绊。低头一看,竟是那张曾化作纸船的道歉信残片,不知何时从井中漂回岸边。他拾起,发现背面多了几行小字,笔迹苍劲,却陌生无比:
>“我曾以为跳崖是终结。
>后来才懂,那是我第一个真正的问题。
>承光留笔。”
风过,残片化灰,随雨落入井中。
翌日清晨,天空降下一场奇异的雨??每一滴雨里,都裹着一颗微小的问心莲种子。它们落在屋顶、田野、坟墓、庙宇,甚至落在沉睡者的唇上。凡是被种子触碰之人,都会在梦中听见一个声音:
>“你还记得,你心里那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吗?”
醒土,自此花开遍野。
而那盏油灯,依旧长明。
不是因为它永不熄灭,而是因为,总有人愿意在黑暗中,再一次问:
“我们……还想要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