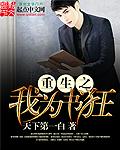笔趣阁>内娱整顿系统来了!libahao.c > 第531章 开启短剧时代彻底改变娱乐圈生态(第2页)
第531章 开启短剧时代彻底改变娱乐圈生态(第2页)
没有人说话。
那一夜,田昕薇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草原上,四周站满了人??有南极科考员、贵阳留守儿童、哈尔滨临终老人、敦煌守窟人、三亚渔民、挪威极地研究员……还有无数面孔模糊的身影,穿着不同民族服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围成一圈,手拉着手,齐声低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
歌声响起时,地面开始震动,裂缝蔓延至天际,岩层翻涌,露出亿万年来封存的记忆:战争、饥荒、离别、爱而不得、死不瞑目……全都被压缩成一声声嗡鸣,顺着地核传导,汇入宇宙背景辐射之中。
她惊醒过来,发现帐篷外月光如洗,而“归墟亭”顶部的陶笛竟在轻轻震颤,发出肉眼不可见的波动。
她立刻联系周沉:“把全球七座亭的数据通道全部打开,我要做一次全域同步接收。”
“风险很大。”他警告,“一旦形成跨大陆共振,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心理连锁反应。有些人可能因此崩溃。”
“也可能因此重生。”她说,“让他们听见彼此。”
凌晨三点,指令下达。
七座“归墟亭”同时启动全频段开放模式。信号不再局限于本地传播,而是通过地下水脉、大气电离层、地磁波道,形成一张覆盖整个星球的情绪神经网络。刹那间,无数未曾出口的话语冲破时空壁垒:
-一位叙利亚母亲在废墟中呢喃儿子的名字;
-东京地铁里,上班族在拥挤车厢中默念“我不想上班”;
-巴西亚马逊雨林深处,原住民长老对着篝火诉说森林消亡的预兆;
-纽约养老院里,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突然清晰地说出亡妻的生日;
-上海某写字楼顶层,白领女子撕碎辞职信,对着夜空大喊“我不幸福!”
这些声音原本永不会相遇,此刻却被“归墟”系统捕捉、转化、放大,最终汇聚成一股浩瀚的情感洪流,直冲地球电离层。
卫星数据显示,那一夜,极光在全球多个非极地区域短暂出现:墨西哥城上空泛起绿光,撒哈拉沙漠边缘掠过紫红涟漪,甚至赤道附近的新加坡居民也报告看到天空中有银色丝线飘动。
而在西藏羌塘,“归墟亭”周围的冻土圈开始缓慢扩张,形成一朵直径达两百米的巨大冰花图案。地质雷达探测显示,其下方岩层中正生成一种新型矿物晶体,成分未知,但具备极强的声波储存能力,科学家日后将其命名为“忆钙石”。
三天后,系统自动关闭。所有设备进入休眠状态。
田昕薇疲惫不堪,却异常清醒。她知道,这一夜改变了很多事。不是世界变好了,而是人们终于意识到:痛苦不必独自承受,真实值得被听见。
多吉找到她,递上一条手工编织的五彩绳结。“这是我们族里的‘心链’,”他说,“送给能把亡者话语带回人间的人。”
她接过,系在手腕上。
一周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急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归墟现象”是否应纳入《人类精神遗产保护名录》。与此同时,多家跨国科技公司秘密组建联盟,试图复制“霜语”技术用于商业情绪干预市场,却被发现所有模拟实验均以失败告终??机器可以模仿声音,却无法伪造那份来自大地深处的回应。
林晚发来最新情报:“澄心会残余势力仍在活动,他们在非洲建立了地下监听站,企图截获‘归墟’声流进行逆向解析。但我们已经布置了干扰源,他们会听到一万个人在哭泣,却永远找不到源头。”
田昕薇看完信息,抬头望向远方雪山。
她知道这场战争还没结束。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痛苦,而是拥有说出痛苦的权利。而“归墟亭”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被遗忘的声音,都能在时间尽头得到一次回响。
傍晚,扎西送来一封信,是用藏文书写的,附带简单汉语注释:
>“你说亭子能让大地听见我们。我想问问,能不能也让死去的藏羚羊听见?我想告诉它们,我们会一直守下去。”
她握笔良久,最终写下回复:
>“它们早就听见了。否则,风怎么会每年春天都吹开花瓣?”
夜幕降临,新一批材料运抵。周沉站在工地图纸前,测算抗高原反应共鸣腔的新参数。田昕薇走过去,轻声问:“下一个选址定了吗?”
他抬头看她,嘴角微扬:“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群矿工想建一座亭子,因为井下常听见已故工友的脚步声。他们说,与其驱鬼,不如请他们坐下来说说话。”
她笑了:“准备出发吧。”
风吹过旷野,拂过尚未完工的“归墟亭”顶端,陶笛发出一声悠长颤音,像是回答,又像是承诺。
而在地球最深的海沟,一只沉睡百年的鲸鱼骨架微微震动,它的肋骨之间,一缕极细微的声波正缓缓苏醒,沿着洋流北上,奔向下一个等待倾听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