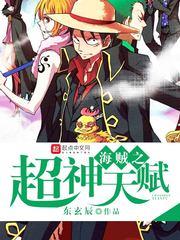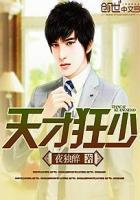笔趣阁>主角许靖央萧贺夜笔趣阁无弹窗阅读 > 第653章 接旨嫁了(第1页)
第653章 接旨嫁了(第1页)
许靖央立刻拱手,垂眸道:“皇上,末将绝无此意,宁王殿下身份尊贵,才德出众,是末将粗陋,恐配不上殿下。”
皇帝脸上的温和笑意淡去几分,化作一种似笑非笑的审视。
“哦?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昭武王,你莫不是……当真看不上朕的夜儿?”
气氛一时有些凝滞。
“父皇,”萧贺夜适时开口,声音平稳,“此事与昭武王无关,是儿臣认为如今边境未定,朝局初稳,远未到考虑成家之时,故而未曾想过婚娶之事。”
皇帝目光转向他:“。。。。。。
春风拂过北岭,吹动山谷中千百盏不灭的蓝灯。远处学堂传来朗朗诵读声:“是谁让我们记得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声音清亮,如溪水穿石,一字一句敲在忆谷深处那座巍峨母碑之上。蓝光微微荡漾,仿佛回应着人间的诵读。
阿禾已逝,可她的名字却从未离开。那一日她闭眼之后,全国笔尖自动书写的铭文久久未能消散,有人抄录成卷,供于家中正堂;有人将其刻入青石,立于村口道旁。更奇异的是,自她离世后,每逢子时三刻,忆谷上空便会浮现出一道淡蓝色的光影,形似老人端坐藤椅,手持炭笔,静静凝望这片她守护了一生的土地。
孩子们说,那是阿禾奶奶在检查名字有没有被风吹走。
而在这片被记忆浸透的大地上,新的故事仍在继续。
忆历三年春,南方青梧村来了一位背着古琴的盲眼少年。他自称江迟之徒,名唤知微,年方十六,双目失明却能辨人心悲喜。他在村中住了下来,每日黄昏坐在老祠堂前,抚琴一曲,不收分文,只求听者讲述一段先祖往事。渐渐地,村民们从最初的冷眼旁观,到后来争相围坐,泪洒衣襟。有人说出祖父曾因拒绝作伪证而被流放岭南,有人说出祖母在饥荒年间割肉喂儿终至饿死……每一句话落下,少年指尖琴音便随之变化,低回处如泣如诉,高昂时似剑破云。
一夜,月圆如镜。少年忽然停手,仰面朝天,轻声道:“师父,您听见了吗?他们开始说了。”
话音未落,琴弦无风自鸣,一声清越直贯苍穹。翌日清晨,村民发现祠堂墙壁竟浮现出一行行幽蓝文字??正是昨夜众人所述之事!字迹清晰,情感真切,连讲述者的声音语气都仿佛藏于其间。有人伸手触碰,指尖竟传来温热,宛如触摸活人记忆。
消息传开,四方震动。各地记名会纷纷遣人前来取经,却发现唯有知微能引动此象。原来,他并非真正盲眼,而是自幼被师父以秘法封住双目,只为让他“不见尘世纷扰,唯见心魂真相”。当他终于开启心眼之时,便是《归魂引》真正传承之始。
与此同时,京畿之地亦起波澜。
真相庭新任监察使林照,乃李婉儿亲选弟子,三十出头,眉目冷峻,行事如刀切水,毫不拖沓。上任伊始,便查出数起隐案:有地方官借“忆历”之名,篡改祖先名讳,将本族罪人美化为忠烈;更有世家暗中销毁族谱,妄图抹去曾参与许氏暴政的记录。林照雷霆出手,连罢七省主官,押送京城受审。
然而,就在她准备推行“全民溯忆计划”??即要求每户人家每年提交一份详实祖先事迹备案??之际,宫中忽传圣旨:暂停该策,待议。
下旨之人,竟是当今皇帝许昭。
此名一出,举国哗然。
许昭,原名沈昭,乃许崇安庶孙,幼时随母隐姓埋名于边陲小镇,十二岁才被寻回宗庙认祖归宗。因其母临终遗言“许家血统污浊,不可承统”,故主动请改母姓,称“沈昭”,后登基时仍执意恢复“许”姓,曰:“我不避其姓,方能洗其罪。”
登基五年来,他废苛政、赦冤狱、重修史馆,表面看是明君气象。可此次叫停溯忆计划,却让许多人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林照连夜入宫质问:“陛下若惧真相浮现,何须当初拨款兴建‘英名录’总馆?若恐民心动荡,又为何允百姓annually诵读先祖之名?”
许昭立于御花园凉亭之中,手中握着一支褪色的蓝羽毛,闻言缓缓抬头:“林卿,你可知我每夜梦见什么?”
“梦里,我站在一片火海之中,四周全是哭喊的人。他们指着我说:‘你是许家人,你该死。’可我从未做过恶……我只是生错了姓。”
林照冷笑:“可你也未曾真正忏悔。你保留许姓,是为了彰显‘改过之勇’,还是为了延续那份血脉正统的幻觉?”
许昭沉默良久,终是轻叹:“你说得对。或许……我仍被困在那个姓氏里。”
三日后,皇帝下诏:开放皇室密档,允许真相庭查阅三代宗亲所有行为记录,并承诺若查出任何隐瞒或包庇,自愿退位让贤。
举国震惊之余,也松了一口气。
但就在此时,一件怪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