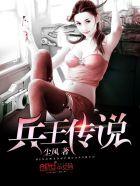笔趣阁>当和尚没前途 >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章 暗尺(第2页)
第一千二百五十七章 暗尺(第2页)
几十人,依次上前。
有人粗手粗脚,却在摸绳那一刻慢了下来;有人本来嚣张,到红绳前竟无声无息。
夜雾像一口慢慢张开的锅,蒸出了人心里的气。
朱瀚负手而立,问:“你们各自报来??一路上,谁走的里程最远;谁挑的货最易坏;谁背的东西最重。”
众人此时已不再争吵,一个个开口。有人说:“我从徽州来,两百里。”
有人说:“我挑的是盐,潮一潮就坏。”
又有人说:“我背的是铁器,一担一百斤。”
朱瀚点头:“远的先,易坏的中,重的殿后。夜里入城,前者轻快,中者稳重,后者护持,不许乱。”
“那如果有人抢呢?”先前那人不甘心问。
朱瀚冷冷一笑,指着红绳:“这绳摸了,就是城门的律。谁越,谁心乱。心乱之人,自己先出错。”
他话音刚落,忽有一个年轻脚夫不信邪,猛地想从侧边绕过,一脚踏进雾里,没想到石板下是湿滑青苔,脚下一空,“噗通”一声摔进了旁边的水沟,浑身湿透。
众人愣了半刻,随后哄堂大笑。
朱瀚淡淡道:“城门夜行,最怕心急。你这一摔,便是‘乱’的样子。
队伍自此安静下来,依照他定下的顺序,列成三行。
雾中,脚步声整齐又不慌乱,像一支夜行的队伍,穿过城门,顺着石板路渐行渐远。
朱瀚看着他们背影,忽然转头,对身侧的朱标轻声道:“你记住了,这不是绳子管人,是人心自定。”
朱标眼里闪着亮光,郑重地点头。
翌日清晨,宫中传来急召。
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见,神色颇为深沉。殿中站着几个重臣,神情不一。
朱瀚与朱标一同入殿,朱元璋一眼扫过,问道:“昨夜城门之事,朕已听闻,做得不错。”
“兄长谬赞。”朱瀚拱手。
“不过??”朱元璋转过身,目光投向大殿正中的地图,“这南市口的法,百姓称心棚”。如今京中大街小巷,皆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你以小术惑众,有人说此法能定人心。你怎么看?”
朱瀚沉声道:“心术,不是术。绳不是神,是人自己给自己的‘尺’。没有尺,百事乱。”
一旁的兵部尚书杨宪却冷哼一声:“王爷言虽妙,可京中人杂事多,这心棚之法,治得了一时,治不了长久。万一人多混乱,红绳岂不成了笑谈?”
朱标忍不住道:“杨大人未免太轻看百姓了!我见棚下的百姓,从最初的不信,到后来自己排队摸绳,井然有序。若人人心中有一尺,岂不比棍棒更有效?”
朱元璋盯着朱标,眼中既有欣慰,也有深意:“太子,你这话我喜欢。但治天下,不能只靠绳子。瀚,你心里有数?”
朱瀚微微一笑:“兄长,绳子只是一个引’。我有后手。”
“说来听听。”
“我准备将心棚之法带入各行各业,不止市井之人,连衙门、军营、学府,都要有一根看不见的‘绳”。但这绳,不是我朱瀚来管,是他们自己来摸。”
朱元璋的眼神变得深邃:“你是想。。。。。。立制?”
“正是。”朱瀚拱手,“此法可小可大。若兄长愿意,我可从军营开始试行。”
殿内众臣一阵低语。有人不安,有人兴奋,有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