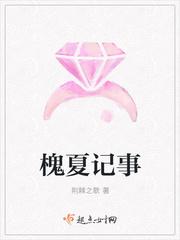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学生平板电脑售后 > 第二百九十四章 杨慎来了杨慎走了(第1页)
第二百九十四章 杨慎来了杨慎走了(第1页)
贾知州离任的场面,与卢昭业那次大同小异。
不过他的官声远好于卢昭业,又有了孝子之名,百姓相送时,真有人舍不得他走,哭声可比合江县大多了。
在最后‘脱靴遗爱’的流程中,贾知州的靴子也被扒了下。。。
夜雨敲窗,烛火微摇。苏春元伏案良久,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未落。窗外雷声滚滚,似天公震怒,又似万马奔腾过荒原。他忽然想起三日前放榜那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赞他胆识过人,也有人暗中讥讽:“这小子不知死活,写什么《河工赋》?贾知州最忌讳提河工弊端,你偏往刀口上撞!”
可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自幼习经史,读圣贤书,不是为了做个唯唯诺诺的应声虫。父亲说得对??可以批判,但不能煽动;可以揭露,但要留余地。而他的《河工赋》,正是以颂为讽,借古喻今。文中引大禹治水“顺乎天地、因势利导”之典,反衬今之河工“逆流筑堰、强征民夫”,更用“童子荷锸赴役,老妪鬻簪输银”之句,道尽百姓血泪。通篇无一激烈言辞,却字字如针,扎在执政者的良心上。
如今提学大人赏识,固然是幸事,但他也清楚:这份赏识背后,藏着更深的试探。一个敢写《河工赋》的秀才,究竟是可用之才,还是潜在之患?若乡试再出此类文章,是擢拔为典型,还是压下作“狂生”处置?
他放下笔,起身推开窗户。风雨扑面而来,吹得衣襟猎猎作响。远处县学的屋檐下,仍有几盏昏灯亮着??那是几位落第的老童生,仍在挑灯苦读。他们之中,有的已考了二十余场,鬓发斑白仍不肯弃;有的家中破产,靠族中接济度日,只为搏一个功名翻身的机会。
读书人的命,从来不只是自己的命。
次日清晨,苏春元换上青布直裰,背起书篓前往州城。院试已毕,距乡试尚有半年,但这段时间最为紧要。提学道既将他列为重点举荐对象,必会召见问策。他必须准备好应对之辞,既不失风骨,又不致招祸。
途中经赤水河堤,景象令人心惊。昔日被征民夫修筑的石坝已有数处崩裂,浊浪拍岸,泥沙翻涌。岸边枯树挂满破布残衣,据说是溺亡者遗物,家人无力打捞,只得焚香遥祭。几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蹲在堤脚挖野菜,见官差模样的人经过,立刻抱头逃窜。
“听说上个月又有三百壮丁调来补工。”同行的一位廪生低声叹道,“工期催得紧,说是贾知州要在秋前向朝廷报‘功成之绩’。”
“可这河性本就湍急,强行截流,岂能长久?”另一人摇头,“我叔父是河道衙门的小吏,说测算图纸全是虚报,什么‘深凿三丈’‘广铺千步’,实则偷工减料,银子都进了监工腰包。”
苏春元默然听着,心中寒意渐生。他终于明白,所谓新政,不过是层层粉饰下的烂疮。上面要政绩,下面便造假;上面要数字,下面便摊派。至于百姓生死,不过是一纸册籍上的勾画而已。
抵达州城时天色已晚,他投宿于城南一家老客栈,店主是个退职的书办,见他是新科案首,格外恭敬,还特地送上一碗热汤面。
“小相公,你是太平县来的吧?”老人一边擦桌子一边问,“听说你们那位海教谕升了州学训导,如今可是人人敬重。”
“正是家师。”苏春元拱手答道。
老人眼神一亮:“难怪你有胆子写那篇《河工赋》!海大人当年在县学讲课,就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今看来,他是把这话传给你们了。”
苏春元心头微动:“您认识恩师?”
“岂止认识!”老人压低声音,“那年我还在县衙当抄录,亲眼见他为赈灾粮单顶撞卢知县。当时卢老爷气得摔了茶盏,说‘你一个小小教谕,也配议政?’海大人当场跪下,朗声道:‘卑职能不能议政,我不知道;但我知,饿死的人会说话,他们的鬼魂会在青天白日里喊冤!’”
苏春元听得脊背发凉,眼眶发热。这些往事,恩师从未提起。
“后来呢?”他轻声问。
“后来……”老人苦笑,“卢知县把他关了一夜,第二天放出来,照旧上课。没人敢提那一夜的事,可从那以后,连衙役见了他都让三分路。”
夜深人静,苏春元辗转难眠。他忽然起身,在灯下展开一张素笺,提笔写道: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今日之世,道隐于尘,义陷于利。使为师者缄口避祸,则学者何所依?使为学者曲笔媚权,则文章何足贵?吾师弘之公,以一身正气立于浊世,如孤峰挺立,虽不见容于当道,终得天地垂鉴。学生春元谨记斯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写罢,他吹熄灯火,静静望着窗外的月光洒在庭院青砖上,像一层薄霜。
三日后,提学道召见。
提学使姓陈,名廷?,乃嘉靖年间进士出身,为人清峻寡言,素有“铁面学政”之称。其衙署设于州城东隅一座幽静书院内,门前两株古槐,枝干虬劲,仿佛守护着一方文脉。
苏春元入堂行礼毕,陈提学并未立即开口,而是久久注视着他,目光如刃,似要剖开皮囊直视心肝。
良久,方道:“你可知本官为何独召你一人?”
“学生不知。”苏春元低头答道。
“因为你写了《河工赋》。”陈廷?缓缓起身,踱至案前,取出一份卷宗展开,“此赋我已细读七遍。初看以为狂悖,再看觉其痛切,三看竟至潸然。你说‘昔禹疏九河,不闻鞭挞百姓;今人障赤水,但见椎髓膏脂’,此语锋利如刀,几乎割破朝堂帷幕。若换作他人,早已以‘诽谤新政’罪名锁拿入狱。”
苏春元伏地不起:“学生愿承担一切后果。”
“不必如此。”陈廷?摆手,“你若真想惹祸,就不会用典如此精微,措辞如此克制。你是懂分寸的??这也正是我看重之处。”
他顿了顿,语气转沉:“可你也该明白,当今之势,非一人之力可挽。贾知州表面推行新政,实则结党营私;朝廷虽有明旨减免赋税,地方却层层加码。你一篇赋文,救不了万千黎庶。若一味刚烈,只会落得身败名裂,连累家族。”
“那该如何?”苏春元抬头,眼中灼灼有光。
“学做流水。”陈廷?指向窗外一渠清溪,“你看那水,遇山绕山,遇石分流,看似柔弱,却能穿岩破壁。你要学会藏锋于文,寄志于诗。将来若登高位,方可真正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