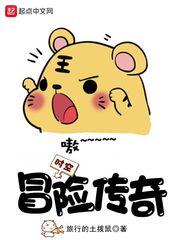笔趣阁>朕真的不务正业txt奇书 >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第3页)
第一千零八十六章 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第3页)
次日清晨,阿禾入宫。
太庙偏殿,赵珩独自等候,龙袍未整,眉宇间透着疲惫。他见阿禾进来,起身相迎,却不说话,只递过一份战报。
阿禾接过一看,脸色微变。
战报记载:陈武昭起兵后,并未攻城略地,反而开仓放粮,释放冤囚,召集百姓议事,并发布《十问檄文》:
>一问:赋税三倍于祖制,为民还是为库?
>二问:官员三代世袭,百姓何日可出头?
>三问:律法明载‘杀人偿命’,为何皇亲杀人仅罚俸?
>……
>十问:陛下自称爱民如子,可曾有一日与农夫同食粗饭?
更令人震惊的是,檄文末尾署名并非“逆贼陈武昭”,而是:
>**“信火学院庚戌级毕业生,曾任皇家武备院教习,现向母校请教:我错了吗?”**
阿禾读罢,久久无言。
赵珩低声问:“你觉得呢?”
她抬头看他:“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
赵珩苦笑:“我十年励精图治,减税赋、清贪官、兴学堂……我以为我已经做得够好。可现在我才明白,我一直在按自己的理解‘为民做主’,却从未真正问过:**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主?**”
他踱步至窗前,望着宫墙外隐约可见的民居炊烟:“或许……我不是救世主,只是一个不肯放手的掌权者。”
阿禾轻声道:“你不需完美,只需诚实。承认自己不懂,比假装全知更接近圣明。”
赵珩猛然转身:“那我该怎么办?派兵剿灭,还是赦免招安?”
“都不是。”阿禾摇头,“你应该下罪己诏,公开回应他的十问,然后邀请他入京,不是以罪臣身份,而是以‘民间问政代表’之名,参加即将召开的‘天下共议会’。”
“什么?”赵珩震惊,“让叛将与三公九卿同席?百官岂能服?”
“若不服,就让他们也提出十个问题。”阿禾直视他,“真正的共识,不是压出来的,是吵出来的。你怕的不是陈武昭造反,是万马齐喑之后,突然有人敢大声说话。”
赵珩怔立良久,终于长叹:“你说得对……这些年,我太习惯听赞美了。连谏官上书,也都小心翼翼,唯恐触怒龙颜。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没人反对,是所有人都觉得‘反对没用’。”
他提笔欲书,却又停住:“可若开了这个口子,今后人人都举兵来问,怎么办?”
“那就说明你问得太少,听得太少。”阿禾淡淡道,“预防暴乱最好的方式,不是筑高墙,是开大门。让问题在阳光下辩论,而不是在暗夜里发酵。”
赵珩沉吟许久,终提笔写下:
>**“朕躬有罪,无以掩之;朕教不明,致忠臣疑惧。
>兹设‘问政台’于午门之外,凡天下士民,皆可具疏陈情,三日内必得回复。
>陈武昭所提十问,朕将亲撰答复,颁行全国。
>并诏其入京共议新政,以彰言路之广,民心之重。”**
诏书既成,快马传檄四方。
七日后,陈武昭率三百亲卫抵达京城,未带兵器,人人手持纸鹤。城门守将本欲阻拦,却见百姓自发列道迎接,孩童争相献花,老农跪地叩首,泣曰:“将军代我们说了三十年说不出的话。”
赵珩亲迎至朱雀门外,脱下龙袍外氅,披于陈武昭肩头,朗声道:“你不是叛臣,你是朕迟来的镜子。”
当夜,皇宫设宴,不奏雅乐,改为“问答之夜”。君臣围坐,每人抽取一只盲盒纸鹤,读出其中问题,当场作答。有问“宫女为何不得婚嫁”,有问“科举为何不用白话”,最尖锐一问来自一位小太监:
>“陛下常说‘视宦官如家人’,可为何家人能娶妻生子,我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