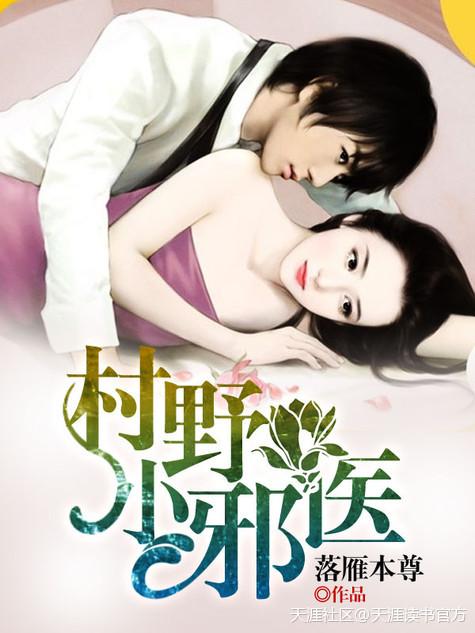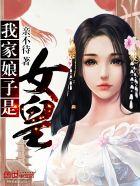笔趣阁>朕真的不务正业txt奇书 > 第一千零九十六章 道理枯燥又乏味不如直接上手段(第2页)
第一千零九十六章 道理枯燥又乏味不如直接上手段(第2页)
殿内死寂。
老太监吓得扑通跪地,连连磕头:“娘娘饶命!奴才只是传话,不敢违抗天威啊!”
赵承熙盯着小禾,良久,忽然笑了。笑声由低转高,竟带几分悲怆。
“好……好一个‘撕掉遮羞布’!”他大步走向书案,抽出那份黄绫奏折,二话不说投入炭盆。火焰腾起,映红了他的脸。
“烧了。”他说,“不但烧,还要下诏申斥礼部尚书,罢其职半年,闭门思过。从此以后,凡敢以‘稳定’为名压制民声者,视同欺君。”
小禾深深一拜:“陛下此举,胜过千言万语。”
赵承熙扶她起身,语气郑重:“现在,告诉我,那张地图在哪里?”
小禾从怀中取出油布包裹,轻轻放在案上。“它不在任何地方,也不在所有人手里。它活在一百零七个‘声音窖藏’之间,每个窖藏都掌握一部分信息,唯有全部汇合,才能还原全貌。林婆婆设此局,防的正是权力篡改或独占。”
皇帝点头:“所以,你要朕证明自己值得信任。”
“不是信任您一个人。”小禾目光坚定,“而是证明这个位置,还能承载希望。”
自那日起,宫廷内外悄然生变。赵承熙下令拆除宫门前象征“肃静回避”的铁牌,改为悬挂“闻民之声”匾额;每日早朝前增设一刻钟“无声听政”??即由宦官朗读十封随机抽取的平民来信,百官静听,不得打断。更有甚者,他亲自主持编纂《庶民语录》,收录街头巷议、农谚渔谣、工匠口诀,命翰林院注解刊行,称“治国不在典籍堆砌,而在烟火人间”。
与此同时,“共视计划”全面铺开。信火派遣三百余名“声音使者”奔赴各地,携带便携式录音陶筒与速记竹简,专录冤案、苛政、隐疾。其中最震动朝野者,乃河北一县令强征“晴雨税”之事:凡遇干旱,百姓须缴“祈雨费”;逢涝灾,则另收“避洪捐”。使者暗访半月,录得七十二户人家哭诉,制成《雨税哀辞》巡回宣讲。该县令闻讯欲捕人灭口,却被当地学堂师生围堵衙门,齐诵《公民问答录》第三章:“官之所赋,必有法度;无诏之征,即是劫掠!”
风波直达御前,赵承熙震怒,下旨将该县令革职流放,并追查幕后庇护者。刑部尚书因包庇亲属涉案,被当场摘去冠帽,押赴大理寺候审。史载:“士大夫始知,今上非虚应故事,实欲刮骨疗毒。”
然而风暴并未止息。冬至前夕,京城突现诡异流言:“信火勾结外邦,图谋颠覆。”随之而来的是匿名揭帖、街头涂鸦,甚至有孩童在庙会上被人塞纸条,上书“你娘听信火蛊惑,迟早遭天谴”。更严重的是,三处“声音窖藏”接连失联??江西庐山洞窟被人投毒烟熏封,浙江雁荡山藏书岩穴遭雷击焚毁,唯一线索是一枚刻着“清源”二字的青铜印章。
小禾召集骨干彻夜研判,最终锁定幕后黑手:清源社。
这是一个百年隐秘组织,表面推崇“纯儒正统”,实则操控科举、渗透官僚、豢养死士,历代皆以“匡扶纲常”为名,行压制异端之实。他们视信火为乱党,认为“妇孺议政、匹夫干政”乃是礼崩乐坏之兆,誓要铲除。
“他们不怕明刀明枪。”陈文昭咳着血分析,“怕的是看不见的光。所以他们要用污名、恐惧、孤立,把我们变成‘妖言惑众’的代名词。”
小禾冷笑:“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显形’。”
于是,“千灯行动”再度升级,推出“真相反向直播”??邀请江湖戏班、说书艺人、佛道僧侣,在各大城池同时上演《清源罪谱》连台本戏,以唱词、评话、傀儡戏等形式揭露该组织百年罪行:包括制造文字狱、陷害忠良、操纵粮价、私设牢狱等。每一幕结尾,均由一名受害者亲属登台作证,手持实物证据,面向人群高呼:“这不是戏,这是我家的命!”
舆论如沸,民心激愤。短短半月,全国涌现上百起自发搜查“清源据点”事件。有老秀才翻出祖辈日记,指认某书院山长曾参与构陷忠臣;有商贾交出账本,显示多年被迫向“清源坊”缴纳“学问税”;更有边关老兵联名上书,控诉该组织曾勾结敌国,泄露军情以换取政治利益。
赵承熙趁势出手,成立“肃清司”,授权小禾为首席监察使,赋予其调阅档案、传唤官员、独立取证之权。三个月内,清源社核心成员被捕四十七人,牵连罢免各级官吏二百余人,抄没田产八万余亩,尽数充作“民声基金”,用于资助贫寒学子、修缮乡村书院、设立流动听证车。
一场腥风血雨过后,朝野为之一清。
春分那日,赵承熙亲赴信火书院,宣布一项空前举措:自明年起,每年三月十五定为“民声节”,全国放假一日,各地举行“无禁忌议事大会”,无论身份贵贱,皆可登台发言,内容不受审查,记录不得销毁。他还当场签署《言权保障令》,明文规定:“凡因言获罪者,主审官连坐;凡压制建言者,无论品级,一律削籍为民。”
典礼结束时,小禾登上钟楼,再次拉动铜铃。
“当??”
一声响罢,四野寂静。
随即,东岭、西谷、南圩、北寨,一处处村落陆续响起回应铃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仿佛大地本身在呼吸。
当晚,小禾独坐院中,仰望星空。陈文昭坐在轮椅上,由仆人推来,怀里抱着一只新制的陶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