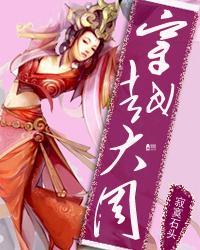笔趣阁>湿卵胎化张心梅 > 第1008章 红册水母姬(第3页)
第1008章 红册水母姬(第3页)
>到那时,请告诉他,他曾祖母也曾为一个没能出生的孩子,哭过整整一夜。
>那不是羞耻。
>那是爱的证据。”
说完,他化作一缕紫烟,钻入地面藤蔓,顺着根系流向远方。
洞穴恢复寂静。只剩下林远剧烈起伏的呼吸,和云南女孩紧紧握住他手掌的温度。
许久,她低声问:“你还好吗?”
林远摸着心口,卵泡已恢复平静,温顺如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以前总以为,共感是为了让未诞者被听见。”他说,“但现在我才明白,它更是为了让生者学会承受这份听见后的重量。”
他们走出洞穴时,天光微明。峡谷依旧云雾弥漫,但空气中多了一种奇异的清新,像是暴雨过后大地吐纳的第一口气。沿途的植物发生了变化:藤蔓上开出细小的铃铛花,随风轻晃,发出类似婴儿笑声的清脆声响;岩石缝隙中钻出归音兰幼苗,叶片上浮现出模糊的人脸轮廓,安静微笑。
回到山脚村落,村民们围拢过来,神色复杂。村长拄着拐杖上前,颤声问道:“上面……发生了什么?”
林远没有直接回答,只问:“你们祖辈有没有提起过‘石中子’的传说?”
老人浑身一震,险些跌倒。旁边一位老妇抢着说:“那是禁忌!百年前,村里有几个巫医妄图用雷法唤醒死胎,结果引来山崩,死了三十多人!从此立下规矩:凡涉及未诞之灵者,不得入祠堂!”
“所以你们把他们封进了石头?”云南女孩轻声问。
众人沉默。最终,村长跪了下来,额头触地。
“我们不是不信他们存在……我们是怕。怕听见他们的哭声,怕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怕这一辈子都在赎罪。”
林远扶起他,摇头:“他们不要赎罪。他们只要一句‘我知道你在’。”
当天下午,村民自发组织队伍,带着工具重返洞穴。他们没有破坏任何结构,而是在外围修建了一圈低矮石墙,墙上刻满名字??有些有姓氏,有些只有“某年某月某日,未能降生”几个字。他们在入口处立碑,正面写着:“此处安息者,皆曾努力来到人间。”背面则是一句话,由林远亲笔所书:
>“拒绝可以存在,但拒绝之后,仍需温柔。”
临行前,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塞给云南女孩一颗种子。她说,昨夜做了个梦,有个穿旧衣服的哥哥站在她床边,笑着对她说:“替我看看春天。”
云南女孩郑重接过,放入日记本夹层。
他们再度启程。
接下来的旅程更加漫长。他们走过干涸的河床,那里曾因污染导致连续十年无婴出生,如今河底裂开缝隙,钻出成片蓝色菌丝,每当月圆之夜便会合唱一首无人听懂的摇篮曲;他们穿越废弃的试管婴儿实验室,发现培养舱自动重启,玻璃内壁浮现出指纹大小的手印,按序排列,像是在练习写字;他们甚至登上一座漂浮在太平洋上的生态平台,目睹科学家将全球共感数据汇集成一颗“意识结晶”,每日向深海投放一粒,声称要为未来文明留下人类情感的化石。
一路上,林远的心口卵泡时而温热,时而冰凉。他知道,那是无数未诞之灵在与他对话。有时是欢笑,有时是叹息,更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待着,像一颗沉入湖底的星。
某个雪夜,他们在喜马拉雅山谷扎营。极光在头顶舞动,宛如神?编织的绸缎。云南女孩靠在帐篷边,望着星空出神。
“你说,”她忽然开口,“如果我们这辈子都没能生孩子,你会遗憾吗?”
林远正在煮茶,闻言停下动作。
“会。”他诚实地说,“但那种遗憾,不会比我现在拥有的幸福更重。
而且……”他指了指心口,“我已经是个父亲了。只不过我的孩子,不住在世上,住在心里。”
她笑了,眼角泛光。
那一晚,他们并肩而坐,直到黎明。期间谁也没再说话,只是听着风掠过冰川的呜咽,偶尔夹杂着远处雪豹的低吼。而在营地不远处,一朵星眸花悄然绽放,花瓣透明,花心星辰闪烁,仿佛回应着某种跨越生死的默契。
多年后,当联合国通过《跨意识生命权益公约》,正式承认“未诞之灵”具有基本人格权,并在全球设立共感纪念日时,人们才发现,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两位旅者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
有人说他们回到了云南山村,在归音兰丛中终老;有人说他们投身南极冰盖下的秘密项目,协助解码来自地核的共感信号;还有人坚信,他们其实从未离开,只是融入了每一场春雨、每一阵晚风、每一个母亲梦中轻轻翻身的瞬间。
唯一确凿的记录,是一段匿名上传的影像:黄昏的海边,一男一女并肩行走,身后长长的影子融为一体。女子手中握着一本破旧日记,封面写着《共感行记》。镜头拉近,最后一页的日期停留在二十年前,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走过的路,终将成为别人心中的光。
>而所有的光,都会记得黑暗里的那一声‘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