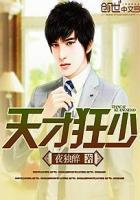笔趣阁>激荡1979txt免费阅读 > 第494章 魏平安 谁是爹来谁是儿(第2页)
第494章 魏平安 谁是爹来谁是儿(第2页)
周老头摇头:“她们不算军人,也不算正式编制,大多是临时工、合同工。出了事,最多发点抚恤金,登个内部通报。外面根本不知道。”
孟波一页页翻着,忽然停住。一张照片让他呼吸一滞??画面中的女子戴着厚厚眼镜,手里拿着电码本,眼神坚定。姓名:韦玉梅,广西南宁人,1965年入伍,服役于西南军区通讯连,1973年退役。
这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在腾格里采访时提到的那位摩挲电码本的老人!她在信中说自己“只是个接线员”,但从这份档案看,她曾多次在战备状态下连续工作四十八小时以上,因过度疲劳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
而在她的卡片背面,竟贴着一张剪报复印件??《解放军报》1971年一则简讯:“某部通讯连成功保障边境演习通信畅通,受到上级嘉奖。”文中提到了连长、指导员,却未提及任何女兵姓名。
“我们活成了影子。”孟波喃喃道。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两侧挂满空白相框。他伸手去摸,指尖触到冰冷玻璃,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吉克阿依、马金花、陈秀兰、李桂芬、张素芬、赵桂香、吴月琴、王亚妹……她们一个个走来,手中捧着自己的照片、日记、勋章、工具。
她们一句话不说,只是把东西放进相框。然后转身离去,身影逐渐淡去,如同晨雾消散。
他惊醒时,天还未亮。手机屏幕亮着,是团队实习生发来的消息:“老师,我们在湖南找到了一个人。她说她认识您找的周秀兰老人。她叫田招娣,八十二岁,曾是抗美援朝后勤车队司机。”
孟波立刻回拨,接通后听见一个沙哑却有力的声音:“我是田招娣。我跟周秀兰在一个医疗转运站待过四十天。她救过我的命。”
原来,1951年冬天,田招娣驾车运送伤员途中遭遇空袭,右腿重伤失血过多。是周秀兰连夜手术止血,又用自己的血输了三百毫升。“她比我小六岁,可看着像个妈。”
“她总说,‘战场上不分男女,只有活着和死去’。”田招娣回忆,“有一次炸弹落在帐篷边上,大家都趴下,她却站起来往火场跑。我说你疯了吗?她说:‘里面有孩子!’”
她保存着一张合影??几个女兵围坐在雪地里吃饭,周秀兰蹲在一旁削土豆,脸上沾着泥点,笑得灿烂。“我一直藏着这张照片,不敢给人看。那时候说‘个人崇拜’不好,我说我喜欢周秀兰,人家说我思想有问题。”
“现在我想通了。”她语气坚决,“我要让她被人记住。不只是作为‘英雄’,而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会疼、会哭、会害怕,但依然选择往前冲的人。”
挂断电话后,孟波打开文档,新建一页,标题写下:“她们的真实”。
他知道,这场追寻早已超越纪录片本身。它不再是为了完成一部作品,而是为了偿还一种亏欠??对那些用青春与生命奠基时代,却被时代轻轻抹去姓名的女人。
他想起清华大学演讲那天,那个学生问他:“普通人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现在他有了答案:能。只要你愿意倾听,愿意记录,愿意把一个名字、一段声音、一份记忆,从遗忘的深渊里打捞上来。
几天后,《大地留痕》项目迎来第一百位受访者??九十四岁的沈玉芳,浙江绍兴人,1950年代首批赴新疆支边女青年。她一生未婚,育有六个收养的孩子,全是在戈壁滩上捡来的弃婴。
“那时候条件苦啊。”她坐在藤椅上,阳光洒在银发上,“奶粉没有,我就挤羊奶喂。衣服破了,拿麻袋改。可孩子们都活下来了,还上了学。”
她拿出一本相册,里面全是泛黄的照片:沙漠中的土坯房、孩子们举着课本奔跑、一家人围坐吃馕……最后一张是去年全家福,子孙满堂,三十多口人。
“有人说我傻,一辈子给别人养孩子。”她笑着说,“可我觉得值。你看,这一代代传下去,不就是希望吗?”
拍摄结束时,一个小孙子跑进来,递给她一部手机:“奶奶,你的视频上热搜了!”
屏幕上显示着一条短视频:标题《她不是母亲,却是千万孩子的娘》,播放量已破两千万。评论区热评第一写道:“这才是真正的奉献。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让这个世界多一点温暖。”
沈玉芳眯着眼看了半天,忽然流泪:“我以为没人记得我了。”
当晚,孟波收到一条系统通知:由《她们的名字》系列衍生的公益基金正式成立,首笔善款来自一位匿名捐赠者,金额五百万元。附言写着:“给我母亲正名。她曾是三线工厂的焊工,烧瞎了一只眼,却从未抱怨。”
与此同时,教育部宣布将“平民记忆特藏室”内容纳入高中历史选修课试点教材;共青团中央发起“寻找祖辈的勋章”主题活动,号召青少年采访家中长辈;多家出版社启动“无名者口述史丛书”出版计划。
而最让孟波动容的,是一封来自新疆伊犁的信。寄信人是个十六岁的维吾尔族女孩,名叫古丽娜尔。她在信中说:
>“我奶奶看了你们拍的沈玉芳奶奶的故事,哭了很久。她说:‘我们也这样过来的。’她告诉我,1962年大饥荒时,她和一群女知青徒步一百公里送粮进牧区,路上饿得啃树皮,还要防狼。她们救了七个快要断炊的毡房家庭。
>
>我从来不知道这些。现在我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叫《奶奶的脚印》。老师说可以投稿参加全国青少年征文大赛。
>
>孟叔叔,我想让您知道,您的片子,让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我的奶奶。”
孟波读完,久久不能言语。
他走到窗前,推开玻璃。春风拂面,带着泥土与新芽的气息。远处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而在这光的背后,有多少沉默的灵魂仍在等待被讲述?
他拿起录音笔,按下录制键,轻声说:“今天是2023年4月17日。我又想起了1979年。那一年,中国开始改变。但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声号角,而是一次次弯腰俯身,去听那些微弱却坚韧的声音。
她们亦曾年轻。
而我们,终于学会了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