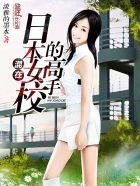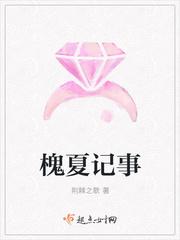笔趣阁>大哥说我天下无敌在线阅读 > 第315章 恐惧(第1页)
第315章 恐惧(第1页)
“拿去!”
“快滚!”
军士们朝着那些人丢下吃的,再次驱赶,那些人就按着杨玄感所教授的,跪在远处,嘴里高呼万岁。
宇文士及骑着马,站在一旁,看着远处那些人,忍不住长叹了一声。
。。。
杨玄感随那白衣人步入密林,脚下枯叶碎裂之声??作响,四野寂静得仿佛连风都凝滞了。身后两名护卫紧握刀柄,目光警惕地扫视四周,却未见半点敌意踪影。林深处,一座简陋草庐隐于古木之间,檐下悬着一盏青纱灯,微光摇曳,映出几道人影。
“请。”白衣人侧身让路,语气温和却不容推拒。
杨玄感略一颔首,抬步而入。草庐内陈设极简,仅有一案、两席、一炉香。案后端坐一人,身形清瘦,头戴竹冠,身披素袍,眉目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静之气。他见杨玄感进来,并未起身,只是轻轻抬手:“杨郎将远道而来,辛苦了。”
杨玄感心中一凛,此人竟不以礼相待,反倒似早已料定他会来此。他不动声色,拱手道:“阁下何人?为何知我行程?”
那人微微一笑:“天下大事,皆有征兆。你欲联李建成共图大业,岂能瞒过有心之人?我姓王,单名一个通字。”
杨玄感瞳孔微缩??王通!河东大儒,曾三拒征召,闭门讲学,门下弟子如魏徵、杜淹皆一时俊彦。此人虽不仕朝堂,然声望之高,连皇帝亦曾亲书诏令欲聘为国子祭酒,却被其婉拒。如今竟在此地现身,绝非偶然。
“王先生隐居多年,何故插手乱世之争?”杨玄感沉声问道。
王通轻拂袖角,淡淡道:“非我插手,而是天命使然。隋室气数已尽,暴政横行,百姓倒悬,此乃天地易主之时。你杨玄感出身将门,文武兼备,又有雄心壮志,本可成中兴之臣。可惜……”他顿了顿,语气陡转,“你走错了路。”
“错在何处?”杨玄感冷笑。
“你欲结李建成,借唐国公之势起兵,看似稳妥,实则迂腐。”王通道,“李渊父子表面恭顺,内藏野心,其志不在救民,而在取而代之。你若与之联手,不过为其前驱,功成之后,必遭清算。昔年韩信辅刘邦得天下,终不免鸟尽弓藏,你不鉴之乎?”
杨玄感默然片刻,冷笑道:“那依先生之见,我当如何?独自举事?还是束手就擒,任裴蕴罗织罪名,将我灭族?”
“非也。”王通起身,踱至窗前,望向远处晋阳城头隐约可见的烽火台,“当今之世,唯有真命之人方能定鼎乾坤。此人不在长安,不在洛阳,而在晋阳。”
杨玄感眉头一皱:“你说的是……李世民?”
“正是。”王通缓缓转身,目光如炬,“李建成虽有器量,然优柔寡断,难当大任。真正可托付天下者,乃其弟李世民。年未弱冠,已具帝王之资。他曾对我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今日不取,恐为他人所夺。’此等见识,岂是寻常贵胄所能及?”
杨玄感心头震动,但面上仍不动声色:“即便如此,我又如何能与李世民结盟?他兄长尚且未决,何况其弟?且李渊老谋深算,岂容外人染指家事?”
王通微微一笑:“所以你需要一个人??李靖。”
“李靖?”杨玄感一怔。
“兵部旧吏,裴蕴排挤而出,贬谪边陲。此人精通奇正之道,善断战机,更难得的是,他心中无门户之见,只求明主可托。若得此人相助,无论起兵或守成,皆如虎添翼。”王通说着,从案下取出一封帛书,“这是我亲笔荐信,你可持此前往灵州,寻他归来。”
杨玄感接过帛书,指尖微颤。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推荐信,更是一张通往真正权力核心的通行证。王通此举,等于将整个关陇未来的格局,悄然推向了另一条轨道。
“先生为何助我?”他终于问出口。
王通闭目良久,才低声道:“因为我看得见民心向背。天下苦隋久矣。而你,至少还有几分血性。我不愿再看百姓流离,不愿再听孩童哭母。若有一线希望,我也要试一试。”
话音落下,屋外忽起风雨,雷声滚滚,穿透林梢。
杨玄感深深一拜:“若他日得遂大志,必尊先生为国师,不负今日教诲。”
王通摇头:“我不求名位,只求史书一笔:王通曾劝一人止杀安民。足矣。”
翌日清晨,杨玄感辞别王通,改道西行,直趋灵州。他留下一名心腹继续前往晋阳,假称自己仍在途中,以迷惑可能的监视耳目。他自己则带着李靖的荐信,穿越黄沙戈壁,踏上了寻找这位传奇将领的艰险之路。
与此同时,晋阳城内,柴绍已悄然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