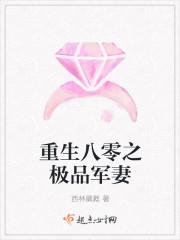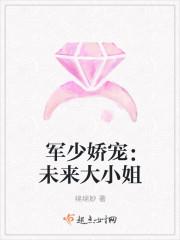笔趣阁>我的饭馆很美味完整版 > 286 大鹏蛋(第2页)
286 大鹏蛋(第2页)
“我……我母亲昨天走了。”他声音嘶哑,“临终前一句话不说,只反复念叨‘想吃一碗葱花蛋炒饭’。我不会做,去饭店点,她说不是那个味。直到今天早上,我在她床头发现这张纸……”
他颤抖着打开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签,上面写着:
>“蛋要打散,油要热,葱花先爆香,盐最后放。炒的时候要说‘乖,趁热吃’,她才肯张嘴。”
屋内一片寂静。
阿满起身,接过锅铲:“来,我教你。”
灶火重燃,油锅滋响。她一步步示范,如何掌控火候,如何让蛋液蓬松如云,如何在最后一秒撒入翠绿葱花。当那碗金黄喷香的炒饭端到李哲面前时,他盯着看了很久,终于低头猛扒一口,随即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
“原来……原来是这个味道……”他哽咽着,“小时候每天早晨,她都是这么说的……‘乖,趁热吃’……”
那一夜,李哲留在了吴记。他不再写批判稿,而是开始记录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故事。他发现,来这里吃饭的,不只是穷人、病人、孤寡老人,还有被裁员的白领、失恋的年轻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饿”得不是胃,是心。
春天渐深,芝麻田已绿意盎然。一天清晨,邮差送来一封加急信件,信封上盖着国务院办公厅的印章。拆开一看,竟是周维亲笔撰写的一份提案复印件,标题为《关于构建“国民心灵膳食工程”的可行性报告》。
文中写道:
>“传统医疗体系难以覆盖心理亚健康人群,建议以‘民间食医模式’为基础,建立社区情感干预厨房网络,培训‘食疗疏导员’,通过共炊共食重建人际连接。初期试点五十城,经费预算暂列……”
附件中,赫然附有吴记的运营模型图,以及“百家炊”“共膳唤醒法”“情绪调味术”等核心技术说明。
小禾看完,轻声问:“他会把我们都变成公务员吗?”
阿满摇头:“不会。因为他明白了一件事??制度可以复制形式,但复制不了温度。”
果然,几天后周维亲自送来一份文件:他申请辞去智库职务,愿以个人身份加入食医体系,成为一名流动食医员,赴偏远山区开展“味道返乡计划”。
“我不懂什么道,”他说,“但我现在知道了,一碗饭的力量,有时比一百份政策文件都大。”
阿满递给他一枚铜牌,上面刻着两个字:“渡者”。
入夏之前,第一茬芝麻成熟了。收割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孩子们踩着小凳榨油,老人们坐在树荫下讲古,笑声与芝麻香一同飘散。油坊开炉那一刻,阿满亲手点燃灶火,火焰腾起三尺高,映红了每个人的笑脸。
当晚,她取出珍藏多年的吴记老账本,在最新一页写下:
>“癸卯年五月十六,芝麻成油,铃声常在。
>周维授徒七人,皆能切丝浮水;
>李哲著《人间烟火录》十三篇;
>《村味录》初稿完成,收录食方三百一十二种;
>全国新增自发食医点四十七处,均无名,唯灶火长明。
>师父曾言:食者,施也。施者,渡也。
>今日方知,所谓渡人,不过是把自己活成一道菜,让别人在咀嚼中,找回失落的自己。”
夜深了,她合上账本,走到院中铜铃下。伸手轻抚铃身,忽觉掌心微热。抬头望去,只见北斗七星正悬于天际,斗柄指向东方,如同一把巨大的勺子,舀起了整片夜空。
她微微一笑,低声呢喃:“该添柴了。”
灶膛里,余烬未冷,新柴已入。火光跳跃,照亮墙上那幅《五谷归经图》,图中五色粮食蜿蜒成河,最终汇入一颗赤红的心脏。
远处,不知谁家的孩子喊了一声:“娘,饭好了!”
回应他的,是一句温柔的呼唤:“来,趁热吃。”
风过处,铃声再响。
叮??
这一声,传得很远,很远。
没有人知道,第二天清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拐立于巷口,望着“吴记饭馆”四字匾额,久久不语。他从怀中掏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铜勺,轻轻放在门槛上,转身离去,步履蹒跚却坚定。
那勺底刻着一行小字:“吴氏炊经,代代相传。”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宋汴梁,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家名为“吴记”的食肆门前,年轻的学徒正扶起一名晕倒的乞丐,轻声道:“别怕,先进来喝碗热粥。”
历史,就这样在一碗饭的温度里,悄然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