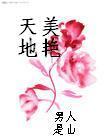笔趣阁>快穿在古早狗血文里兴风作浪TXT > 第3872章 枉死丫鬟女配707(第1页)
第3872章 枉死丫鬟女配707(第1页)
不远处,几位白发老者正相互搀扶着缓步而行。
为首的老丈拄着虬枝拐杖,玄色棉袍的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
他时而驻足细看店铺新挂的鎏金招牌,时而指着某处屋檐对老伙计们低语,想必是在辨认往昔熟悉的痕迹。
跟在后面的老妇人手腕上缠着菩提念珠,时不时伸手抚过绸缎庄外垂落的流苏,浑浊的眼底泛起温柔的光。
“记得那年上元节,这棵老槐树下还搭过三丈高的灯楼呢。”
最年长的老者突然开口,枯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斑驳的树皮。
其他老人闻言都会心一笑,皱纹里漾开的不仅是怀念,更有种阅尽千帆后的从容。
他们走走停停,偶尔在茶摊歇脚,青瓷茶盏里浮沉的不仅是茶叶,还有沉淀了数十载的市井记忆。
当暮鼓声从城楼传来时,老人们的身影渐渐融进斜阳里,唯有拐杖叩击青石的声响,还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君欣治下的城镇里,更是流淌着一种别处难寻的暖意。
这里没有市井常见的算计与防备,街坊邻里相处,倒像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青石板路上传来的不只是脚步声,更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絮语。
记得那日西市口,一位挑着菜担的老汉不慎绊倒。
新鲜的时蔬滚落一地,青翠的菜叶沾上了尘土。
还没等老人撑起身子,已有三四双手同时伸了过来。
卖豆腐的娘子麻利地拾起散落的蔬菜,打铁铺的伙计小心地扶起老人,连对面茶楼的小二都端着热茶匆匆跑来。
众人七手八脚地帮老人重新捆好担子,那娘子还特意从摊上取来清水,将沾了土的菜叶一一洗净。
城东的书肆前,曾发生过这样一桩事。
一位青衫书生突然跌坐在台阶上,原来他的钱袋不知何时被人摸了去。
这外乡学子举目无亲,眼看着连住店的银钱都没了着落。
卖糖画的张老汉最先瞧见,当即从腰间摸出几个铜板。
这举动像是打开了闸门,左邻右舍纷纷围拢过来。
布庄的掌柜塞来一块碎银,卖胭脂的姑娘递上几枚铜钱,连在街角玩耍的孩童都捧来了攒了许久的压岁钱。
不过盏茶功夫,书生的盘缠竟比原先还多出几分。
他捧着这些带着体温的银钱,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对着众人深深作揖,连道“他日必当结草衔环以报”。
这样的情景,在京城里实在算不得稀奇。
酒肆的老板娘总会给巡夜的更夫留碗热汤,药铺的先生常为贫苦人家减免诊金。
就连最忙碌的早市上,人们也不忘互相照应。
谁家有了喜事,整条街都跟着沾喜气;谁家遇到难处,左邻右舍没有不帮忙的。
这般光景,倒真应了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
而朔风掠过曾经染血的城墙,如今只扬起集市上的彩幡。
那些枕着刀剑入眠的夜晚,那些烽火连天的记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化作了老兵酒后的谈资。
边关的清晨不再被战鼓惊醒,而是随着驼铃与商队的吆喝声缓缓苏醒。
记忆中的边陲,黄土里还埋着断戟残戈。老校尉们偶尔会指着某处山坡,说起当年那里曾是如何尸横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