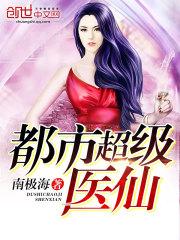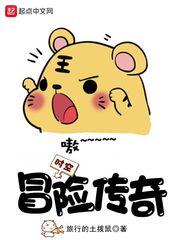笔趣阁>天可汗回忆录全文 > 第546章 没有永远的敌人(第2页)
第546章 没有永远的敌人(第2页)
她转身回屋,提笔修书,命快骑送往长安:
>“请陛下暂缓宗室问责程序。
>臣请设立‘悔改赎偿制’:凡主动呈报隐匿账目、退还非法所得者,视情节轻重减罚,或准以劳役代刑。
>同时开放‘匿名举证通道’,保护揭发者身份,杜绝报复之患。
>共算非刀,乃镜也。照人,亦照己。”
三日后,宫中回音抵达:皇帝准奏,并加一句朱批:“朕亦愿照此镜。”
消息传开,朝野震动。有人称她软弱,纵容贵戚;也有人泪流满面,跪谢苍天尚存仁政。而最令人意外的是,仅仅半月之内,竟有十七位皇亲主动赴京认罪,交出私藏账簿三十余册,退还赃款四百余万贯。
其中一人,正是那位曾借“番邦进献”之名走私南洋珍宝的皇姑母。她在奏表中写道:“臣妹昔年以为,皇家体面高于一切。今见童子军少年李昭秉笔直书,毫无惧色,方知羞愧。宁可家财尽散,不愿子孙蒙耻。”
沈知微读罢,只说了一句:“孩子教大人学会了诚实。”
冬尽春回,终南山桃花初绽。新学堂落成典礼定于三月初三。那一日,千灯齐燃,百官列席,百姓云集。沈知微立于门前,亲手推开那两扇刻有数字序列的青铜大门。当晨曦斜照,右侧原本隐形的真相序列缓缓显现,与左侧官方记录严丝合缝,门轴轻转,轰然开启。
全场寂静,继而爆发出震天欢呼。
典礼之后,她召集所有童子军,在学堂后院举行“薪火传灯”仪式。每人手持一盏铜灯,依次点燃,最后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真”字。李昭作为编号“壹仟零壹”,第一个上前引火。
“你可知道,为何选你?”沈知微问他。
少年恭敬答道:“因我是皇子,却愿低头查账。”
“不全然。”她摇头,“因为你不怕得罪至亲。而这,才是共算最稀缺的品质。”
李昭低头,再抬头时眼中已有泪光:“学生只求,将来治国时,不让百姓再因一句‘为了大局’而沉默。”
她欣慰一笑,将手中火种递出:“那么,请你点燃第一盏灯。”
火焰跃起,映红少年的脸庞,也照亮了身后整座山谷。
数日后,沈知微收到敦煌来信:考古队在碎叶城遗址附近发现一座废弃驿站,墙垣内藏有一口陶瓮,瓮中保存着数十份羊皮卷,皆为当年押送“罪籍妇孺”的沿途记录。其中一份,赫然写着押运官李承业的亲笔日记:
>“丙申年四月十五,夜宿伊州荒亭。
>一小女乞水,我不予。她哭曰:‘叔叔,我不是坏人,我只是娘亲的孩子。’
>我彻夜难眠。
>明日抵戍楼,我将放她们逃走。哪怕因此被斩,亦不愿再做鹰犬。”
然而后续记载戛然而止。据当地老兵口述,那支队伍最终并未逃脱,而是在戈壁深处遭伏击灭口,领队官员当场格杀。唯有一名盲眼女童幸存,被牧民收养,晚年常对孙儿讲述“穿黑袍的大人们如何把好人变成鬼”。
沈知微将这份日记抄录三份:一份送入宗正寺,要求为李承业平反;一份置于共算学堂纪念馆,题为《忏悔的力量》;第三份,则寄给了正在岭南巡查的李昭。
她在附信中写道:
>“你看,连执行黑暗命令的人,也曾有过觉醒的瞬间。
>所以不要轻易定义谁是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