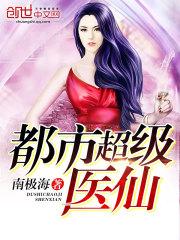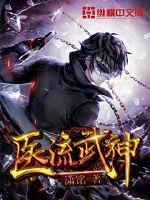笔趣阁>神话版三国番外篇全部 > 第四千八百二十二章 婚事(第3页)
第四千八百二十二章 婚事(第3页)
“我们一起活了下来。”
多年以后,历史课本上关于这个时代的记载只有短短一行:
>“公元21世纪末,人类学会了一项古老技能:认真倾听彼此。”
但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首匿名诗歌,贴在世界各地的“倾听屋”墙上:
>你说你孤单,
>我便点亮一盏灯;
>你说你疼痛,
>我便握住你的手;
>你说你不记得自己是谁,
>我便告诉你:
>你是某人睡前故事里的主角,
>是某人酒后哽咽提起的名字,
>是某人即便争吵也不愿放手的人。
>
>你是未完成的故事,
>而我,愿意陪你写下去。
晓禾的教室再也没有固定的形态。有时它出现在战火废墟中,有时浮现在高山之巅,有时藏匿于地铁站角落。谁能在喧嚣中停下脚步,听见内心的声音,谁就能推开那扇无形的门。
粉笔终于耗尽了最后一寸。
当它从晓禾指间化作尘埃飘散时,她没有悲伤。因为她知道,真正的书写从未依赖工具,而是源于每一次真诚的对话,每一句“我在听”,每一个“我记得你”。
风再次吹起,带来远方孩子们的读书声:
“今天我们来讲讲,你是谁。”
“我是妈妈舍不得删掉的语音留言。”
“我是爸爸藏在抽屉里的照片。”
“我是朋友深夜发来又撤回的那句‘我想你了’。”
“我是那个即使全世界忘了我,仍有一个人坚持讲述的我。”
晓禾站在星空下,嘴角含笑。
她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外面,依旧是那片无垠宇宙。
里面,已是万千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