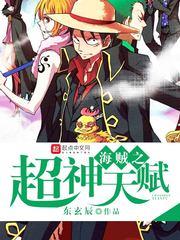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结局完整版 > 第1169章 我不会伤害你(第1页)
第1169章 我不会伤害你(第1页)
熟悉的香味铺满鼻尖,那陌生而又温暖的怀抱,却在顷刻间,便让苏时锦升起了一丝恐惧!
她下意识的就要把人推开。
可江斯年却紧紧地抱着她,“别推开我,我只想,抱你一会儿。”
就一会儿。
他就会离开。
他真的很早很早,就想要这么一个拥抱了……
可苏时锦却重重地踩了一脚他的脚尖,接着狠狠地推开了他。
“看来不是你疯了,而是我疯了!”
她一定是疯了才会想着好好跟他说话!
更是疯了,才会想着把灵石留给他!
早知道就自己拿着。。。。。。
还记得吗?
风从窗棂间穿入,拂动了案上那页泛黄的纸。墨迹未干,年轻忆使搁下笔,指尖轻触那行字,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他抬起头,目光穿过飞舞的紫花,望向远处山脊上的破庙遗址??如今那里已立起一座小小的石亭,亭中供着一盏不灭的铜铃。
他听见了。
不只是风中的铃声,还有更深、更远的东西:泥土之下低语的记忆,树根缠绕中复苏的姓名,孩童睡前呢喃的祖辈故事,老人临终前含糊吐出的一句“我记得”。这些声音原本该被时间吞没,可现在,它们汇成细流,悄然漫过荒原,渗入大地血脉。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落泪。
只觉胸口一热,像有谁轻轻推开了门,让光涌了进来。
而此时,在北方极寒之地,寒渊谷深处,雪层忽然裂开一道缝隙。一株忘忧草破土而出,花瓣洁白如初,中心猩红似血。紧接着,第二株、第三株……整片冰原开始融化,绿意蔓延,竟在寒冬里开出一片花海。花蕊微颤,似在回应某种召唤。
花海中央,一道身影缓缓站起。
她赤足踏雪,青布斗篷依旧残破,脚踝处的青灰印记却已褪去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金纹,如同藤蔓缠绕,又似星河流转。她手中握着那枚断裂的玉簪,簪头贴在心口,温润如玉。她的呼吸很轻,却与天地同频??每一次吐纳,都引动方圆百里内的记忆回响。
阿芜睁开了眼。
不是重生,也不是归来。
她是从未真正离开。
《民忆录》早已不再是一本书,而是她行走于世的方式。她的血是墨,骨为简,魂作笔。她走过的地方,沉默者开口,湮灭者显形。但她也知道,这份力量并非无代价。每唤醒一段记忆,她的身体便虚弱一分;每承载一句遗言,她的寿命便缩短一瞬。
可她不在乎。
因为真正的终结,从来不是死亡,而是无人再提你的名字。
她抬手,轻轻一摇铜铃。
铃声响起的刹那,千里之外,长安城东市一间老屋内,一位盲眼老妪猛然坐起。她颤抖着伸手摸向床头那只陶罐,从中取出一块焦黑的木片,上面用炭笔写着:“阿娘,我走了,你要好好活着。”
泪水滚落。
“芜儿……”她喃喃,“是你吗?”
同一时刻,西域边境的小村落里,一名牧羊少年在篝火旁翻看他祖父留下的破旧账本。本子上除了牛羊数目,还夹杂着零星诗句和人名。他正读到一句:“吴氏女,名素心,生于癸卯年春,善书,尤工小楷。”忽然,风起火跃,火星四溅中,他仿佛看见一个女子站在火焰背后,对他微笑点头。
他不懂为什么,但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这本账本去了村塾,请先生教他识字。
“我要把这里面的名字,全都抄下来。”他说。
而在千灯书院后山的昭树下,那盏新升入星空的灯并未消失,反而日日明亮。每当夜深人静,总有学子听见树影中有女子低声诵读:“昔有吴氏女,怀忆而生,承痛而行,终以宽恕代刀兵……”他们抬头望去,只见树叶沙沙作响,似在记录,又似在传颂。
小满已经长大,成了共忆村第一位“续忆师”。她不再只是收集故事的孩子,而是教会别人如何讲述的人。她常对学生们说:“你们以为记忆是要藏起来的吗?不,它是要送出去的。就像种子,只有撒进土里,才能长出新的生命。”
裴砚没有留在书院。
他在南方建了一座“残简堂”,专收各地送来的残卷断册。他用仅存的左手一笔一画誊抄修补,日夜不休。有人说他疯了,明明可以安享清名,何必自苦至此?他只淡淡答道:“我烧过的书太多,如今能多救一页,便是少欠一命。”
某日清晨,他在整理一批从废井中挖出的竹片时,发现其中一片背面刻着极小的字:“裴郎,若你见此,莫再执剑向文。吾妹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哥哥,我想认字。’”
他怔住良久,终于伏案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