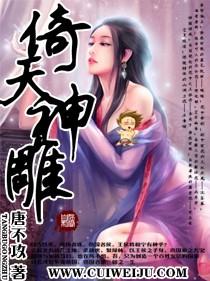笔趣阁>毒妃她从地狱来结局完整版 > 第1169章 我不会伤害你(第2页)
第1169章 我不会伤害你(第2页)
那天之后,他开始收徒授学,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愿记、愿写、愿说,皆可入门。他还立下规矩:每月初一,全堂上下必须共读一本最不起眼的民间手札??可能是农妇记的菜谱,也可能是乞丐写的梦话。他说:“最卑微的文字里,藏着最真实的历史。”
十年过去,共忆运动席卷九州。
朝廷再也无法封锁“异端之籍”,因为百姓家家户户都在写自己的家史。有人将祖辈遭遇编成唱词,在街头传唱;有人把族中女性事迹绣在布上,挂于厅堂;更有甚者,凿山为碑,刻下被删改的战事真相。官府派人查禁,却发现根本抓不完、烧不尽??昨日毁去一本,明日就有十人背诵流传。
皇帝曾试图重启净魂司,却被群臣联名劝阻。礼部尚书跪奏:“陛下,昔日焚书以绝乱源,今民皆自书其忆,若再镇压,则恐天下人心尽失。”连曾经最忠于皇权的老臣也低声补充:“臣家中幼孙,每晚必讲‘阿芜姐姐的故事’,若我们今日动手,明日他便不再唤我一声‘爷爷’。”
皇帝沉默良久,最终下令:废除《禁忆令》,开放民间修史之权,并拨款兴建“九州共忆馆”。
消息传出,万民欢腾。
唯有皇宫深处,那位白发苍苍的帝王独自坐在御书房,翻阅着新呈上的《民忆录?续编》。书中不仅记载了吴素心的冤案,还有无数他曾下令抹杀的人物与事件。他的手微微发抖,却未合上书页。
他知道,这不是背叛,而是偿还。
他提笔,在扉页写下四个字:**吾亦记得**。
然后,他起身走向昭树,亲手点亮了一盏新灯。
灯火升空,融入星河。
与此同时,阿芜正行走在西南边陲的群山之间。这里曾是“断语岭”,传说凡踏上此地者,三日内必失所有记忆。如今瘴气散尽,石壁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刻痕??全是过往旅人临死前挣扎留下的名字与话语。
她伸手抚过那些凹陷的笔画,指尖渗出血珠,滴落在岩缝中。瞬间,整座山岭震动起来,无数光影浮现空中:一个男子抱着婴儿逃亡的身影,一名女子在烈火中高喊“记住我的名字”,一群百姓跪地哀求“求您留下一本书”……
她闭上眼,轻声问:“你们还想被人记得吗?”
风停,云开,群山齐鸣:
>**想!**
她笑了。
转身之际,她看见山坡上有位小女孩正怯生生望着她,怀里紧紧抱着一本破书。
“你是……阿芜姐姐吗?”女孩小声问。
“你怎么知道我?”她蹲下身。
“因为我奶奶说,她梦见一个穿青布斗篷的姐姐,走遍天下找名字。她说,那个人会来救我们的记忆。”
阿芜心头一震。
她接过那本书,封面已被磨平,只剩半个“忆”字。翻开内页,竟是用蝇头小楷抄录的《百家姓》,但每一页都被细细标注??哪些姓氏已在官方户籍中消失,哪些家族后代流落何方,哪些女人的名字被强行改为“某氏”。
这是民间自发编纂的《寻亲录》。
她抚摸着纸页,忽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心悸。胸口那团热意猛地翻涌,像是《民忆录》在体内觉醒到了极致。她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
她撑着石壁缓缓坐下,从怀中取出那枚断裂的玉簪,放在掌心。
“时候到了。”她对自己说。
不是结束,而是交接。
她咬破指尖,以血为引,在玉簪断口处画下最后一道符??正是母亲吴素心所创的“忆契咒”终极形态。这不是束缚,不是传承,而是一次彻底的释放。
“我不再是容器。”她低声念道,“我是桥梁。”
话音落下,玉簪骤然发光,化作点点金尘,随风飘散。每一粒微光都裹挟着一段记忆,飞向四面八方。有的落入村庄学堂,有的坠入孤坟碑前,有的嵌进孩童枕边的布偶眼睛里。
她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
皮肉之下,经络化作文字流淌,骨骼浮现篇章轮廓,心脏跳动的节奏,竟与千万人口中诵读的句子完全同步。
她没有痛苦,只有平静。
因为她看见??
北方,裴砚正在教孩子们写字,忽然抬头望天,似有所感。他手中的笔停顿片刻,落下两个字:**芜归**。
南方,小满站在讲台上,面对百余名学生,开口第一句便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宽恕的故事。”
西方,那位黑袍女子再次翻开金边书籍,这一次,书页自动翻至末章,浮现一行新字:**她选择了人间**。
东方,海边渔村的老渔民对着孙子讲述“那个摇铃的姐姐”时,海浪突然退去,沙滩上留下一行清晰足迹,直通礁石尽头??那里,一朵忘忧草静静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