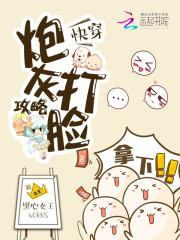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结局 > 第450章 来得比他这个当爹的还快(第1页)
第450章 来得比他这个当爹的还快(第1页)
姜心棠霎时心神一荡,忙问:“小世子不是在睡觉吗,怎么会不见了?”
方才萧迟走时,那小子没有出现。
她还把照顾小儿子的嬷嬷叫去,问小世子怎么没来送他父王。
嬷嬷说她一早就去叫小世子起床了。
但小世子说他昨晚想到父王要离开,难受睡不着,现在很困,还想睡。
萧迟作为父亲,听完很动容,让嬷嬷别吵小儿子,让小儿子继续睡,不用来送他了。
可怎的这小子突然就不见了?
宫婢说:“王爷走后,嬷嬷回了小世子屋里,就见小世子。。。。。。
夜雨初歇,檐角滴水如断线珠子,敲在青石阶上,声声入耳。沈明远披衣起身,推开东阁小窗,只见庭中棠树湿漉漉地立着,枝叶低垂,似负千钧。归名潭面浮着薄雾,水光幽暗,倒映不出星月,却隐隐有微光自潭底渗出,如同谁在深处点了一盏长明灯。
他凝视良久,忽觉袖口一沉,低头见那片昨夜落于肩头的四色花瓣仍在,颜色未褪,触手温润,竟似活物呼吸般微微起伏。他心头一颤,轻声道:“先生,可是有什么未尽之言?”
话音刚落,风动树梢,一片叶子飘然坠下,恰好落在窗台上。叶脉清晰,竟显出字迹??非墨所书,而是天然纹路拼成三字:**往南去**。
沈明远怔住。这三字不似寻常指引,却与《海隅篇》末页一行小注遥相呼应:“南海有岛,名‘忘忧’,非图所示,唯心诚者可至。”当年念棠先生未曾亲履此地,仅凭梦中渔女吴阿妹一声呼唤,记下此语。众人皆以为虚妄,唯有陆承安曾言:“名字能渡海,魂亦能引路。”
他当即取笔,在残稿边空白处添上一句:
**风示南行,或为新录之始。**
次日清晨,沈明远召集书院弟子议事。九鼎虽熄,但归名之责未止。近来各地忆名坛上报异象频仍:岭南某村每至子时,井中有童声诵《采莲曲》;西北荒原一夜之间生出百株白棠,花蕊中藏细小骨片,经辨认为百年前战死戍卒遗骸;更有东海渔民捞起一具沉船木箱,内藏竹简数十片,字迹模糊,唯见反复出现“**请记得我**”四字。
“这些名字,尚未入录。”沈明远道,“而先生留下的三册遗稿已尽,新魂仍在呼唤。我们不能再等。”
众人默然。有人低声问:“若再开鼎,泥土何来?九方之土早已燃尽。”
沈明远望向南方天际,缓缓道:“不必九方。此番南行,只为一方??海土。”
三日后,一艘小舟自书院后溪出发,顺流而下,入江,汇海。舟上仅五人:沈明远、两名抄录弟子、一名通晓潮汐的老渔夫,还有一只陶瓮,盛着从归名潭底取出的旧灰烬??那是前次仪式后未散的余烬,据传仍存灵性。
航程艰险。越往南,海色越深,浪涛如怒龙翻脊。第七日夜,星辰隐没,海面突现荧光点点,宛如星河倾泻。老渔夫惊呼:“这是‘鬼火海’!传说亡魂聚处,水会发光!”
话音未落,远处海平线上浮起一座岛屿轮廓。无山无林,唯见白沙环抱,中央一株孤树矗立,形如棠,却通体银白,叶片泛蓝,花开四色,却寂静无声。
“忘忧岛……”沈明远喃喃,“它真的存在。”
登岸时天将破晓。沙地柔软,踩上去不留痕,仿佛行走于云上。那株银棠树下,立着一块无字碑,碑前堆满贝壳、碎瓷、褪色布条??皆是人间琐物,却被精心排列成圆阵,似某种古老祭仪。
沈明远跪地捧沙,细看之下,沙中竟混有极细微的骨粉,与珊瑚砂交融,形成奇特纹路。他取出随身携带的棠枝笔,蘸以归名潭灰调制的墨,在纸上轻轻一点。
墨迹未干,空中骤然卷起旋风,沙粒飞舞,拼出第一行字:
**林六娘,十八岁,?家女,善织网,能歌。咸丰七年海啸,全家覆舟。临终抱一破陶罐,内藏幼弟乳牙。今每逢潮退,岸边可见其影独坐礁石,哼摇篮曲。**
笔尖微颤,沈明远疾书其名。写罢最后一划,银棠树忽然抖动,一朵四色花飘落,触地化作一枚贝壳,壳内刻着同一段文字。
第二名随之浮现:
**陈石头,十岁,孤儿,随船漂泊。疫发时全船染病,唯他活至最后,靠啃食帆布苟延。死前用炭条在舱板写下:‘我想有个家。’今夜半常闻空船吱呀,似有人推门而入。**
第三名、第四名……接连不断,如潮水涌来。有的名字带着哭腔,有的只剩气音,有的甚至无法成句,唯有“疼”“冷”“饿”三字反复回响。沈明远不停书写,手指冻裂,血渗入墨中,纸页渐染红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