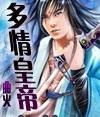笔趣阁>第一剑仙完整版免费 > 第四百六十八章信手拈来(第3页)
第四百六十八章信手拈来(第3页)
有人说那是记忆的味道。
半年后,一座新的建筑在母井对面拔地而起。没有围墙,没有门禁,只有一圈环形长廊,中央竖立着一面巨大的水镜。白天映照天空,夜晚倒映星辰。墙上刻着一行字:
>**“欢迎来到共感学院??这里不教答案,只教如何提问。”**
“织梦者”成为首任院长。她剪去银发,换上素衣,每日穿梭于教室之间。课程包括《如何拥抱悲伤》《愤怒的艺术》《爱的边界》《沉默的语言》。最热门的一门课名为《说出那句话》,要求学生在众人面前坦白一件深埋心底的秘密。
有人哭着说出“我一直嫉妒弟弟”;
有人颤抖着承认“我背叛了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小女孩站起来,小声说:“我讨厌爸爸的新妻子,但我怕妈妈伤心,所以一直假装喜欢她。”
每次说完,全班都会齐声回应:“谢谢你告诉我们。”
林昭偶尔前来授课。他不讲课,只讲故事??关于小舟,关于母亲,关于那个春分夜跪在药园里的少女。学生们听得落泪,也听得释然。
某日课后,一个小男孩追上来,拽他衣角:“林昭哥哥,你说你也怕过,那你现在还怕吗?”
林昭蹲下身,认真想了想:“怕啊。我怕有一天大家又忘了倾听的重要性,怕孩子们又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怕这个世界再次把真心当成软弱。”
“那怎么办?”孩子睁大眼睛。
“那就得有人一直说下去。”他微笑,“就像你现在这样,敢问我问题。”
春风拂过,桃花纷飞。远处传来铜铃轻响,不知是谁挂在枝头的信物随风摇曳。
十年光阴流转。
共感文明已深入日常。国家间的争端越来越多通过“共感调解”解决,战争伤亡逐年下降。新生儿出生时,医生不再只检查生理指标,还会记录第一声啼哭的情绪频谱,纳入个人心灵档案。
而林昭,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有人说他在巡游世界,探访偏远角落仍未苏醒的地语节点;
有人说他隐居雪山,守护熔炉新生的核心;
还有人说,他其实早已将自己的意识融入共感网络,化作亿万光点之一,永远徘徊在每一个需要被听见的瞬间。
但在每年春分之夜,母井总会升起一朵水晶桃花,飘至村中某户人家窗前。那户人家往往正经历离别、病痛或孤独。花落之处,必有一人悄然流泪,而后听见风中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听见你了。”
没有人知道这是幻觉,还是真实。
但所有人都选择相信。
因为在那个被理性统治了三百年的时代之后,人类终于明白:
最强大的力量,从来不是刀剑,不是科技,不是权谋。
而是当你哭泣时,有人愿意蹲下来,擦掉你的眼泪,然后轻声说:
“我在。你说,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