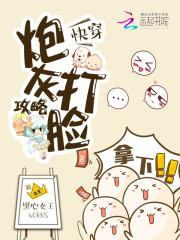笔趣阁>这个明星正得发邪 无错 > 第436章(第1页)
第436章(第1页)
星耀传媒里。
郭伟诚看到网上的消息后有点坐不住。
不是说好的顺其自然力压陆燃一头呢。
不是说顺其自然最擅长主旋律歌曲的创作呢?
这首《黄河大合唱》怎么看都像是顺其自然的风格啊。。。。
江水拍打着船身,发出轻缓的节奏,像是大地的脉搏。陆燃摘下耳机,将刚刚录下的旋律回放了一遍,眉头微皱,又按下重来键。这段主歌还不对劲,太柔了,少了点东西??不是气势,而是重量。黄河是咆哮的,长江却是深沉的,它不怒而威,不动声色地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奔流。
他低头看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草稿,《长江组曲》第一乐章暂定名为《源起》,灵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冰川融雪。可怎么用音乐表现一滴水从雪山之巅坠落、汇成溪流、终成大江的过程?他试过用钢琴模拟水珠落地的清脆,也尝试用低音提琴铺陈出地壳运动的厚重,但总感觉缺了一环??那是一种“活着”的气息。
“你得听见它的呼吸。”孙恺的声音突然从岸上传来。
陆燃抬头,看见孙恺正踩着码头边的木板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却掩不住眼里的光。“我刚从金沙江回来,”他在船头坐下,拧开盖子倒出一碗热腾腾的姜汤,“那边的老船工说,长江会说话,夜里静下来,靠在岸边听,能听见它在唱。”
陆燃接过碗,没急着喝,只是盯着江面出神。“他们唱什么?”
“不知道,听不懂,但心会颤。”孙恺咧嘴一笑,“就像你那天在演播厅里念‘中华民族的儿女啊’,没人教你该怎么念,可你一张嘴,所有人都觉得??就该是这样。”
陆燃沉默片刻,忽然笑了:“所以你是让我别写谱子,先去听江?”
“不然呢?”孙恺反问,“黄河是你改出来的,可长江不能改,它只能被唤醒。你得顺着它的脾气走,而不是让它顺你的节奏。”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一阵号子声,粗犷苍凉,穿透晨雾而来。一艘老旧的货轮缓缓驶过,船头站着几个穿着雨衣的工人,正齐声喊着川江号子。那声音沙哑却有力,像铁链拖地,像山石滚落,却又奇异地与水流共振,形成一种原始而庄严的律动。
陆燃猛地站起身,抓起录音笔就往船尾跑。“快!录下来!”他一边按着按钮一边喃喃自语,“这才是源头……这才是活着的音乐!”
孙恺摇摇头,笑着跟过去帮忙固定设备。等那一艘船彻底远去,录音结束,陆燃已经双眼发亮,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和弦走向。“听到了吗?那个‘嘿哟??嗬’的拖腔,不是为了省力,是为了对抗急流!每一个音高都在变化,因为水流在变,情绪也在变!这不是表演,是生存!”
“所以你要做的,不是一首交响诗,”孙恺说,“是一次溯游。”
陆燃点头:“我要沿着长江走一遍。从沱沱河到入海口,每一站都采风,每一段都记录。我要让《长江组曲》不只是音乐,而是一部声音地图。”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孙恺语气认真起来,“这可不是综艺彩排,没有团队支持,没有安保,也没有退路。你得坐最慢的绿皮车,住cheapest的客栈,甚至可能几天没信号。”
“正好。”陆燃把录音笔收好,目光投向远方,“我想看看,除了热搜上的中国,还有什么地方,还在唱没人听的歌。”
三天后,陆燃独自背上行囊出发了。没有官宣,没有随行人员,甚至连社交媒体都没更新。只有孙恺知道他的行程:第一站,青海玉树,通天河畔。
高原反应来得比预想更快。刚下飞机,陆燃就觉得脑袋像被铁箍勒紧,呼吸短促。当地接待他的是一位藏族音乐学者扎西才让,五十多岁,满脸风霜,说话慢条斯理,却句句戳心。
“你们汉人总说长江源头在格尔木,其实不对。”扎西递给他一杯酥油茶,“真正的源头,在牧民的心里。我们小时候放牛,听到冰川裂开的声音,就知道春天来了。那声音,比任何乐器都准。”
当晚,他们在帐篷里围炉夜谈。扎西拿出一把牛角胡琴,拉了一段古老的“格萨尔王”史诗调。旋律悠长悲怆,仿佛穿越千山万水而来。陆燃听得入迷,忍不住拿起吉他试着合奏,却被扎西笑着打断。
“你弹得太规整了,”他说,“我们的音乐没有节拍器,只有心跳。你得跟着风走,跟着羊群走,跟着经幡飘的方向走。”
那一夜,陆燃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逆流而上,穿过激流险滩,越过悬崖瀑布,最终抵达一片洁白无垠的冰原。在那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冰湖边吹骨笛,笛声清冷如月光,每一声都唤醒沉睡的雪线。
醒来时天还未亮,他立刻打开录音机,凭着记忆记下那段旋律。那是《源起》的副主题,终于找到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辗转于长江上游各大支流之间。在四川康定,他跟随一支民间山歌队翻越折多山,在海拔四千米的垭口上录制了一场即兴对唱;在云南丽江,他拜访了一位纳西族东巴祭司,学会了用古羌语吟诵《创世纪》片段,并将其融入组曲的引子部分;在湖北宜昌,他蹲守三峡大坝泄洪口整整两天,只为采集那一声惊天动地的水啸。
每到一处,他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们心中,长江是什么?”
答案五花八门:
“是我阿妈洗菜的水。”
“是洪水来时推走我家房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