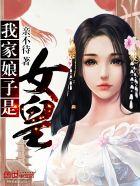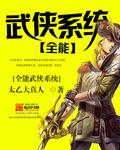笔趣阁>这个明星正得发邪 无错 > 第436章(第3页)
第436章(第3页)
这里曾是新中国最早的造船基地之一,如今厂房斑驳,铁锈遍地,唯有江风依旧呼啸。他租下角落一间小屋,白天走访退休老工人,晚上整理素材。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师傅听说他在写长江,颤巍巍地拿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里面全是当年建造万吨轮时的笔记,还有他自己编写的《船工号子集》。
“现在没人唱了,”老人叹息,“年轻人嫌土,嫌累,嫌不够‘潮’。”
陆燃翻开那本手抄本,一页页看下去,忽然发现其中一段旋律,竟与《黄河大合唱》里的某个动机惊人相似。
“您这调子,是从哪儿学的?”他问。
“祖上传的。”老人说,“说是百年前,长江上的纤夫们就这么喊,既能统一步伐,也能驱散恐惧。后来抗战时,有些战士就是听着这号子上前线的。”
陆燃心头一震。
原来,黄河与长江,早就在人民的歌声里汇流了。
他当即决定,在《长江组曲》终章加入一段复调结构:以川江号子为基底,融合黄河怒吼的节奏型,再由童声合唱团演绎新版《保卫长江》,歌词由沿途采集的真实话语拼接而成。
当他把这个构想告诉孙恺时,对方久久无言,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已经不是在做音乐了,你是在缝补记忆。”
六周后,陆燃抵达上海。这里是长江入海口,也是整趟旅程的终点。他没有选择在豪华音乐厅首演,而是联系了浦东一处滨江社区中心,提议举办一场“平民音乐会”。
消息传出,报名人数瞬间爆满。参与者不限年龄职业,只要愿意分享自己与长江有关的故事或歌声,就能登台五分钟。
演出当天,现场坐满了三百多人。有退休教师讲述她曾在江心洲教书三十年的经历;有快递小哥唱起老家九江的采莲曲;还有一个十岁男孩,用电子琴弹奏自己改编的《长江之歌》,虽然跑调严重,却赢得全场掌声。
压轴时刻,陆燃走上简陋的舞台,身后站着临时组建的十五人乐队??包括一名环卫工人、两名外卖骑手、三位小学生、一位盲人按摩师,以及那位来自玉树的扎西才让。
灯光很弱,音响也不专业,但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源起》以一段冰川融水的滴答声开场,随后牛角胡琴缓缓切入,如同晨曦初照雪峰;
《奔流》用急促的鼓点模拟激流碰撞,电吉他撕裂般划破空气,象征现代文明的冲击;
《城与舟》则是一段爵士与民谣交织的慢板,描绘都市灯火与归航渔船的共存;
而终章《同饮一江水》,全场观众自发打开手机闪光灯,随着合唱轻轻摇晃,宛如星河流淌于江面之上。
最后一个音落下,寂静持续了足足半分钟。
然后,掌声如雷。
没有欢呼,没有尖叫,只有深深的敬意与共鸣。
几天后,《长江组曲》全篇正式上线。平台标注:“本作品所有收益将用于长江生态保护基金及民间音乐传承项目。”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黄河到长江,一条精神长河的奔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专程来华会见陆燃,表示愿将《听见长江》田野录音档案作为补充材料,提交至“世界记忆遗产”候选名录。
而在一切喧嚣之外,陆燃又一次回到了长江边。
这次是在江苏南通的一片湿地。他坐在芦苇丛中,看着夕阳沉入江海交汇处,耳边播放着最新采集的一段声音??一群孩子在岸边捡垃圾,一边干活一边唱歌,调子歪歪扭扭,却是他自己写的《保卫长江》童声版。
他笑了笑,关掉播放器,轻声哼起新的旋律。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孙恺发来的消息:
“下一个,你想写什么?”
他望着渐暗的天际线,打了三个字,又删掉。
重新输入:
“我想写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