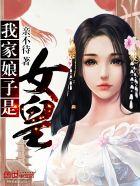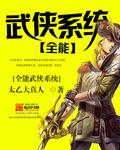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学生平板电脑官网 > 第三零六章 岳父亦是父(第1页)
第三零六章 岳父亦是父(第1页)
兵备府后衙,书房。
黄珂坐在正位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从外头进来的苏录。
心里头那点别扭劲儿还没散,可眼睛却骗不了人……这小子真是越长越出挑了。跟去年比,个子肉眼可见地蹿了一截,肩膀也撑得更开。。。
钟钧承将密信置于烛火之上,火舌舔舐纸角,墨迹蜷曲成灰,随风飘散。他并未立刻下令查办,亦未召人问询,只是静坐良久,目光沉入案前那份朱批名录之中。苏录二字,赫然列于榜首,红印如血,不容更改。院试已毕,功名既定,生员之籍已入黄册,非轻易可夺。然此子才高志锐,锋芒外露,又值朝中党争暗涌、学政清浊难分之际,一封无名之书,虽不足为据,却足以种下疑根。
三日后,提学道衙门传出消息:新科案首苏录,准其入府学肄业,然须于月内赴提学署亲聆训诫,以正心术。众人皆知,此非嘉奖,实为警示。往届案首,不过差人送帖贺仪,何曾有亲聆训诫之例?分明是大宗师欲当面折其锐气,察其本心。
苏录接旨时神色如常,只拱手称谢,退而焚香沐浴,备文书礼服,不发一言。胡大厨忧心忡忡,夜半推门入室,见他伏案抄写《大学》章句,笔力沉稳,毫无滞涩,忍不住低声道:“少爷,这训诫……怕是有杀机啊!那封黑信谁写的?县尊大人如今也不来了,莫非也怕沾上是非?”
苏录搁笔,抬眼望月:“是非自有公论,我心光明,何惧暗箭?若因言获罪,则圣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训,岂非虚语?然我既执笔应试,便知文章不止为修身,更为立世。立世者,岂能避责逃议?”
胡大厨听得心头一震,竟觉这少年言语之间,已有庙堂气象,再不敢多劝。
次日清晨,苏录束发戴巾,着青布直裰,腰系素绦,足踏皂靴,背负书匣,步行赴城西提学署。沿途百姓闻讯,纷纷驻足观望,有人低声赞曰:“真儒者气象!”亦有老学究摇头:“可惜了,这般人才,怕是要被压下去。”
提学署门前古柏森森,石狮踞守,门吏验过文书,引他入仪门,穿回廊,直至明伦堂侧一间静室。室内陈设简朴,唯有一案、两椅、一炉香。钟钧承已端坐其中,未着官袍,仅披深青学士氅衣,神情肃穆。
“苏录,见礼。”
“学生拜见大宗师。”苏录躬身行礼,动作不疾不徐,毫无怯意。
钟钧承示意其坐,良久方开口:“你可知今日为何召你前来?”
“或因文章涉政,恐有妄议之嫌。”苏录坦然对答。
“大胆!”钟钧承拍案,“寻常生员,敢如此直言?”
“学生不敢欺瞒。”苏录抬头,目光清澈,“策问乃问治道,若避讳现实,徒作空谈,则与腐儒何异?朝廷设科取士,原为求实才,非豢养鹦鹉。”
堂内一时死寂,连香炉中升起的青烟都似凝住。钟钧承盯着他,眼中怒意未消,却又夹杂一丝难以察觉的激赏。他缓缓起身,在室中踱步数圈,忽而转身:“你说水利当因地设渠,官督民办,可有实例佐证?”
“有。”苏录不假思索,“浙西山阴诸县,旧有鉴湖遗制,民自筑堰蓄水,灌溉千顷,唐宋以来赖之。后官府强收归管,年年征夫修堤,耗银无数,反致淤塞废弃。此即‘官办不如民办’之明证。”
“那你可知,若地方自专水利,豪强势必兼并水源,弱民受害更深?”
“故须立约法,设乡老评议,官府备案稽查,非放任不管,而在调控得宜。”
钟钧承默然良久,终是轻叹一声:“你年纪轻轻,思虑竟如此周密。然则……”他语气微沉,“才高易傲,言直招祸。你文章中‘河工虚耗钱粮’六字,看似议论制度,实则影射近年漕渠重修之事。那工程由户部督办,监工乃京中权要亲信。你此举,无异于指桑骂槐。”
苏录垂目:“学生但据所知而言,不敢影射任何人。若有冒犯,愿领责罚。”
钟钧承凝视着他,忽然冷笑:“你以为我不知你底细?你父苏伯安,原非农夫,而是前朝太医院吏员,因拒附权宦刘瑾党羽,贬谪返乡,隐姓埋名二十年。你母亦出自婺州经学家门,通《诗》《礼》。你自幼受双亲熏陶,十三岁便能讲《春秋》三传,十五岁注解《孟子章句》,何曾真是寒门野士?”
苏录心头一震,面上却不改色:“先父确曾任职太医,然早已解职归田,一生清贫守节。学生所学,皆赖家训与书院师长教诲,并无特殊门路。”
“好一个‘并无特殊门路’。”钟钧承冷声道,“可你师承不明,平日所读,不止程朱集注,更有王通《中说》、陆九渊语录,甚至私藏李卓吾《藏书》残卷??这些,可是正统儒生该看的?”
苏录终于变色:“《藏书》乃禁书,学生从未得见!至于陆氏心学,不过偶闻讲论,略作参详,未尝奉为宗旨。”
“不必狡辩。”钟钧承挥手打断,“我查过你在府城听讲笔记,多次引用‘心即理也’‘发明本心’之语,与朱子格物穷理之说相悖。当今圣上崇朱学,黜异端,你若执迷不悟,纵有才华,亦难容于庠序!”
苏录沉默片刻,忽而起身整衣,再度长揖至地:“大宗师所言极是。然学生以为,圣人之道,贵在践履,不在门户。程朱主敬持诚,陆王重心明觉,皆不失为求道之路。今人拘于一家之言,排斥异己,致使学问僵化,士风萎靡,岂非舍本逐末?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因学术微歧而废英才,则非所以弘道也。”
钟钧承怔住,久久不语。窗外秋风掠过庭院,吹动檐角铜铃,叮咚作响。他望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二十未满,身形清瘦,却脊梁挺直如剑,言语间无半分谄媚,亦无丝毫退缩。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如此??敢于质疑师说,不屑阿附权贵,最终却被贬出京,困守南荒十余年。如今位高权重,反倒成了当年最厌恶的那种人。
“你走吧。”他终是挥袖,“案首之名不变,入学照准。但从今日起,每月初一须来提学署呈交读书心得,不得缺席。若有违逆言论,立即革除功名,永不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