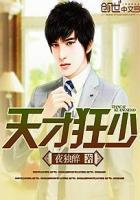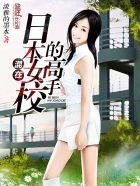笔趣阁>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123读书网 > 第330章 夺其功名且修书去(第2页)
第330章 夺其功名且修书去(第2页)
会场一片寂静。
宋弘业起身回应:“她所言极是。权力若无制衡,哪怕出自善意,也会腐化。我提议设立‘监察使团’,由各阶层随机抽选百人,任期一年,独立调查各地施政,有权罢免渎职官员。”
立即有人反对:“随机抽选?岂非让无知百姓决定国家大事?”
“正是如此。”苏婉儿冷笑,“你们怕的不是无知,而是失去控制。可别忘了,正是你们口中‘无知’的农夫,供养了你们的学堂与诗会。”
争论再起。直到一名年逾七旬的老农拄拐上台,他是山西代表,名叫陈老实,一生未识字。他掏出一块破布,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我要说话。”
“俺不懂啥宪章条款,”他声音沙哑,“但俺知道,去年村里分田,里正把好地给了他侄子,坏地分给寡妇。现在你们说要‘共治’,可要是没个俺这样的人盯着,谁替俺们看住那些笔杆子?”
全场动容。
最终决议:成立“百姓名察院”,赋予其与议会同等的舆论监督权,且每项政策推行前,必须在十个试点村落公示七日,接受普通民众质询与修改建议。
制度渐成,人心初聚。
但真正的试炼,来自紫禁城下的那一夜。
太后联合三位藩王,在神机营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承平帝已被妖术蛊惑,另立皇太孙朱允?为帝”,并下令焚烧泉州送来的《七政宪纲》副本,称其“悖逆祖制,惑乱人心”。
消息传至通州,民代表群情激愤,要求武力清君侧。
承平帝却摇头:“若以刀剑开路,我们与旧时代有何区别?”
骆昭建议:“不如启用‘同梦’之力,直入宫闱,唤醒禁军共感。”
少年自昆仑传音:“不可。第九珠未启,强行扩展共梦范围,可能导致集体意识崩溃。且皇宫地底有古阵封锁,梦网难侵。”
就在僵局之际,一只信鸽飞落船头。
信来自紫禁城东六宫??是太后的贴身宫女所写:“娘娘已于昨夜软禁皇后与太子,今晨将举行登基大典。但她不知,奴婢曾听过第七声钟。”
柳红绡立刻召集梦使:“准备‘心语桥’??我们要让整个皇宫听见过去的声音。”
当夜,紫禁城内灯火通明,百官被迫齐聚太和殿。新帝尚未登基,忽闻空中响起无数低语,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百万百姓的记忆回响??
一个饥民啃着树皮说:“我想吃饱。”
一位母亲抱着病儿哭喊:“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
一名老兵跪在坟前:“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换一批老爷!”
更有一道稚嫩童声清晰响起:“奶奶说,皇帝本该是天底下最大的善人,可为啥咱们总吃不上饭?”
满殿文武皆僵。连执刀护卫也眼神涣散,似陷入某种深远梦境。
太后怒吼:“妖术!快敲钟驱邪!”
可当钟声响起,竟与空中回响共振,形成奇异和鸣。那一刻,连她自己都听见了自己少女时的誓言:“愿辅幼主,清明执政,不负黎民。”
她踉跄后退,面色惨白。
就在这时,承平帝的身影出现在太和殿门外。他未穿龙袍,仅着素白长衫,手持一卷《约法十条》,缓步而入。
“母后,”他跪地叩首,“儿臣知您忧国,但您的方法错了。您想守住的‘祖制’,早已成了蛀空梁柱的白蚁。”
太后颤声:“你……你竟敢背叛列祖列宗!”
“我没有背叛。”他抬头,目光清澈,“我只是终于明白,所谓列祖列宗,真正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永不倒塌的庙堂,而是一代代人都能活得像人的世间。”
殿外忽然传来整齐脚步声。
数百名禁军士兵列队而入,却非护驾,而是集体解甲。为首的千户朗声道:“我们听过那个梦。我们不愿再为一座拒绝醒来的宫殿流血。”
太后终于瘫坐龙椅,泪流满面。
次日清晨,诏书颁行天下:
>“自即日起,太后归隐慈宁宫,静思养性。
>皇太孙朱允?改封‘和平侯’,遣往泉州学习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