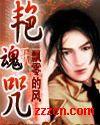笔趣阁>明末我崇祯摆烂怎么了?!笔趣阁无弹窗 > 第331章 朱由检 呜呜呜我是废物(第1页)
第331章 朱由检 呜呜呜我是废物(第1页)
“冤枉啊!温大人,我冤枉啊!大明律有规定,春秋义社无罪,我实无罪也!如果非说我有罪,那我罪在爱国,罪在爱民!
温大人,陛下一定是误会在下了,求大人再为我声张!草民有话要说与陛下听,对,待我痛陈内。。。
夜色如墨,浸透了哀牢山的千峰万壑。云雾在谷底翻涌,仿佛大地吐纳着远古的呼吸。山腹深处,岩浆未冷,赤红的光透过玄武岩的裂缝渗出,映照出一座沉睡千年的地宫轮廓。石门之上刻着八个古篆:**“天命有数,九终启十”**。
第十颗螭龙珠就嵌在地宫正中,半融于熔岩池中央的一根玉柱之内。它通体漆黑如夜,却内藏星河旋转,每一道光丝都似承载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此刻,珠体正微微震颤,与北方紫禁城中的第九珠遥相呼应,如同母子低语。
而在西域,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三百丈,另一座更为古老的遗迹悄然苏醒。第十一颗珠悬浮于一座青铜祭坛之上,周围十二根石柱自发亮起符文,竟是早已失传的西域名??“**阿胡拉?马兹达之眼**”。风沙掩埋的壁画上,描绘着一群身披白袍的人牵着手围成圆圈,头顶浮现出九颗明珠,第十颗则悬于苍穹之外,光芒照耀整个东方。
昆仑之巅,少年猛然睁眼,左瞳中北斗九星骤然明亮,第十、十一颗星点随之浮现,在虚空中勾勒出新的图谱。
“原来如此。”他轻声道,“九珠开启的是记忆与共感,而第十珠……是选择。”
他转身望向东南。泉州港外,承平帝正立于码头,目送一艘艘满载《七政宪纲》抄本的商船驶向琉球、吕宋、安南。这些书籍不再只是治国之策,更成了海外华人的精神火种。一名来自爪哇的华侨老者跪在甲板上,捧书泣不成声:“三百年了……我们终于又有‘家’可归。”
骆昭站在皇帝身旁,低声问:“您真的甘心只做一名象征?”
承平帝笑了笑,目光落在远处一群正在修缮学堂的百姓身上。“你说甘心?我曾握天下生杀予夺之权,却救不了一个饿死街头的孩子。如今虽无实权,但每一条法令出台前,都有百姓名察院的农夫、织妇、挑夫在质询修改??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回归。”
话音未落,柳红绡疾步而来,手中紧握一枚玉简??那是从敦煌莫高窟密室中新发现的“梦使遗卷”。
“第九珠开启后,远古梦网开始复苏。”她神色凝重,“这卷上说,每一颗珠的觉醒,都会引来‘守旧之力’的反扑。前九次轮回,皆因第十珠未启,便遭镇压。这一次……他们不会坐视。”
“他们是谁?”骆昭追问。
玉简上最后一行字迹斑驳:“**影殿不灭,执圭者永存。**”
与此同时,四川净尘社总坛,苏婉儿正主持一场秘密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代表齐聚一堂,许多人脸上还带着风霜与疲惫。一位河南女代表哽咽道:“我们村推行土地改革时,原里正勾结残余厂卫余党,煽动愚民说‘分田是妖法’,纵火烧毁粮仓,打死两名梦使联络员……他们甚至给孩子灌药,让他们做假梦,诬陷监察使团是‘吃人魂魄的邪教’!”
陈老实拄拐起身,声音嘶哑:“这不是个别。我在山西也见到了。那些人打着‘护祖制’旗号,实则怕丢了好处。他们不怕百姓穷,只怕百姓醒!”
苏婉儿缓缓站起,眼中寒光一闪:“所以,我们必须抢在影殿全面反扑之前,将‘共感种子’播入每一个角落。”
她展开一幅新绘地图,上面标注着三百六十五个尚未建立分会的偏远村落。“我们要派‘梦行者’下乡,不是去发令,而是去倾听。让每个村子自己选出三人小组,记录苦难,提出诉求,并通过‘心语桥’接入全国梦网。只要有一人做梦,万人皆可共感。”
有人忧心:“若被影殿渗透怎么办?”
“那就让他们渗透。”苏婉儿冷笑,“我们公开所有流程,接受百姓名察院监督。真金不怕火炼。而且??”她顿了顿,“我要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明白,今天的百姓,已不再是任人蒙蔽的羔羊。”
数日后,第一批三百名梦行者出发。他们中有former锦衣卫密探、白莲教医者、江南女塾教师、蒙古牧民、苗疆巫祝……身份各异,却都经历过至暗时刻,又因共梦而重生。
其中一人,正是当年刺杀承平帝未遂的赵景元。他已放弃复仇,转而投身南方山区的教育重建。临行前,他对皇帝深深一拜:“您给了我父亲清白,也给了我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想帮更多孩子,不必再为一口饭走上绝路。”
皇帝扶他起身,只说了一句:“去吧。把真相种进泥土里,比刻在碑上更久。”
赵景元点头,背起行囊,走入烟雨江南。
就在梦行者们踏上征途的同时,哀牢山地宫之中,第十颗珠终于完全脱离玉柱,缓缓升空。它的黑色表面裂开一道细缝,一道纯净的白光射出,直冲云霄。
刹那间,全国所有接入梦网之人,无论是否在睡眠状态,脑海中同时响起一声钟鸣。
不同于第七声钟的悲怆,也异于第九珠觉醒时的浩荡,这一声钟,清澈如童音,却又蕴含无穷重量:
>“你愿意,为别人多走一步吗?”
无数人停下手中事务。
京城茶馆里,一名算命瞎子突然流泪:“我骗过十八个寡妇的钱……明天,我去自首。”
岭南书院中,一位老儒生撕碎自己写的《驳共和论》:“我骂新政三年,其实……我只是害怕看不懂新世界。”
西北边陲,一名退役千户放下酒杯,召集旧部:“咱们当年为朝廷守边,现在,该为百姓修渠了。”
这一日,史称“**十钟齐响**”。
而真正令人震撼的,发生在三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