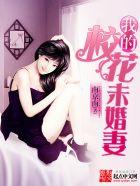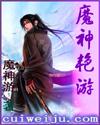笔趣阁>都重生了谁还当演员啊洛珞 > 第783章 互联网战神360网络院线(第1页)
第783章 互联网战神360网络院线(第1页)
三部电影,李明洋最看好的就是这部我的十七岁。
重生题材。
有点夏洛特烦恼那股子味道。
但却不是喜剧。
这是一部弥补遗憾的治愈电影!
张海自己当主角,很多剧情来自他的高中亲。。。
林远站在门口,雪粒子顺着屋檐滑落,在晨光中碎成细小的晶莹。他没有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杨蜜,仿佛怕惊扰了这一刻的寂静。那台老式录音机搁在他臂弯里,像一件圣物,外壳磨损得厉害,边角甚至有些发黑,可按键依旧清脆,指示灯还泛着微弱的橙光。
“这机器……”杨蜜轻声说,“还能用?”
“修过三次。”林远笑了笑,指尖轻轻抚过播放键,“每次坏了,我就找老师傅一点点修。它不只是机器,是活的。”
杨蜜点点头,没再说话。她转身走进书房,从柜子里取出一支崭新的录音笔,又拿出一张手写的卡片,塞进透明夹层里。她把录音笔轻轻放在林远手中。
“现在轮到你听了。”她说。
林远低头看着那支笔,银色外壳上贴着一行小字:“听见,就是爱。”
他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这是……给我的?”
“不。”杨蜜摇头,“是交给你保管的。从今天起,这支笔要跟着你走。去电台,去夜里的直播间,去每一个不敢开口的人身边。你替我按下去,替我听完。”
林远的手微微颤抖。五年前那个雨夜,他蜷缩在天台边缘,风灌进衣领,冷得像是要把骨头吹散。他录下最后一段话,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如果有人听见,请告诉我……我还值得活着吗?”然后他把磁带塞进村小广播站的投递口,像投出一封寄往虚空的信。
他以为没人会听。
可第二天清晨,广播响了。不是音乐,不是通知,而是他的声音??原原本本,一字未改。播完后,一个温柔的女声响起:“林远同学,你值得。而且,你已经被听见了。”
那一刻,他哭得像个孩子。
而现在,这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正把同样的力量递到他手上。
“杨老师……”他声音哽住,“我其实一直想问,为什么是我?那天那么多人路过广播站,为什么偏偏是你打开了那盘带子?”
杨蜜望向窗外。雪已停,朝阳把屋顶染成淡金色。她沉默片刻,才缓缓开口。
“因为我也曾是那个躲在角落里,等着被听见的人。”
她从未对外讲过自己的童年。镜头前的她光芒万丈,可私底下,那个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女孩,常常整夜整夜地坐在阳台角落,听着母亲在屋里哭泣。她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说话,是闭嘴。因为她知道,一旦开口问“妈妈你怎么了”,换来的只会是一句:“大人的事你不懂!”
她于是学会了用声音掩饰情绪。演戏时笑得灿烂,采访时答得滴水不漏。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些年她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为自己说的。
直到三年前,她在怒江村小第一次按下播放键,听见朵朵稚嫩的声音讲述被父亲殴打的夜晚,她突然崩溃大哭。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终于有人替那个小时候的她说了那句:“我害怕,但我还在努力活着。”
“所以当我听到你的磁带,”她转过身,目光清澈如泉,“我知道,那是另一个我在求救。”
林远怔住了。
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声音学校”不教技巧,不设门槛,甚至连课程都没有固定大纲。因为它根本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桥??连接那些破碎的灵魂,让沉默者重新学会呼吸,让呼喊者不再孤单。
“我想加入你们。”他低声说,“不只是送磁带,我想成为导师,成为那个……愿意听的人。”
杨蜜笑了。她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文件。
“我已经为你留了位置。”她将文件递过去,“‘夜间倾听计划’第一期导师聘书。授课对象:城市边缘人群、高危心理个体、夜间工作者。授课形式:匿名热线+实时陪伴录音存档。你愿意接下这个班吗?”
林远接过文件,手指几乎不受控制地发抖。封面上印着一句话:
>“你不需要解决问题,只需要存在。”
他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她:“我愿意。但我有个请求。”
“你说。”
“让我把第一堂课,设在当年那个天台。”
杨蜜愣了一下,随即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