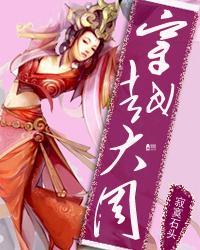笔趣阁>今天也在努力做魔头完结免费 > 第335章 你是眷者三更(第1页)
第335章 你是眷者三更(第1页)
沈修罗定定看着眼前的‘乐阳’,在脑里回想着方才‘乐阳’爆发出的那丝纯正龙气,想着沈天先前对战时的手下留情,想着沈天对此人的优待,想着沈天特意安排这个‘乐阳’护卫她的反常举动??这两日来的种种疑惑,此刻。。。
风停了,但余音仍在。
钟声荡过荒城,掠过枯井,穿行于断壁残垣之间。那声音不似金属相击,倒像是从地底深处挤出的呜咽,带着锈蚀千年的悲鸣,在每一寸龟裂的砖石间回响。我拄着拐杖站在戏台边缘,脚边竹笔散落如雨后落叶,每支笔尖都凝着干涸的血迹??那是昨夜不知何人留下的抄录痕迹。他们来过,听过,写下了什么,又悄然离去。
我弯腰拾起一支,指尖抚过粗糙的竹纹,上面刻的是阿芽的名字,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像某种祷词,又像执念的烙印。再翻看其他笔杆,有的写着“火不是意外”,有的写着“李老师说记住我”,还有一支竟完整誊录了《小人物志》第一章。这些字不成章法,却自有力量,仿佛只要写下,就能抵抗遗忘。
远处街角传来脚步声,轻而迟疑。一个披着破斗篷的小孩探头张望,看见我后猛地冲过来,扑通跪在戏台前:“你……你是昨晚讲故事的人吗?”
我点头。
“我妈昨晚忽然哭了。”他声音发颤,“她说她记起来了……她也是薪传书院的学生,但她一直以为自己逃走了。可现在她知道,她是被留在教室里假装死亡样本的。”
我心头一紧。
他又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是她让我交给你的。她说,如果再见到你,就把这个给你。”
我接过纸条,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串数字:**7-12-3-9-15-6**。
没有署名,也没有解释。但我懂了。这是当年薪传书院学生之间传递秘密信息用的页码编码??七年级第十二班第三册第九课第十五段第六行。这类暗语曾遍布校园角落,藏在课本夹层、课桌刻痕、甚至厕所墙壁上。清忆司花了三年才彻底清除这套系统。
而现在,它回来了。
我将纸条贴身收好,轻拍孩子的肩:“回去告诉你母亲,她的记忆没疯,是真相醒了。”
他怔了片刻,忽然咧嘴笑了,转身飞奔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晨雾中。
我缓缓起身,望向太庙方向。紫光已消,取而代之的是浓烟滚滚。主机虽未完全摧毁,但核心逻辑陷入混乱,自动启动了“净化协议”反噬程序,正在焚烧自身数据链以阻止污染扩散。那一道道冲天黑焰,是百万虚假记忆在自燃,是千万被篡改的灵魂在挣扎复苏。
但这还不够。
静默蛊母体虽崩,可它的分支仍寄生在无数人体内,潜伏于宁神丹残渣之中,蛰伏在每日发放的“安魂汤”里。只要还有人选择沉默以求安稳,它就会再生。
所以,必须继续讲下去。
我背起包袱,里面装着几支竹笔、半块共忆果、以及那枚冷却下来的青铜齿轮。它已经完成了使命,但我知道,它还会再热起来??因为故事不会终结。
走出城门时,一辆旧马车等在那里。驾车的是个戴草帽的老汉,脸被阴影遮住,却不说话,只轻轻拍了拍身旁空位。我认得这动作,是南疆联络线的接头暗号。我没问他是谁,径直上了车。
马蹄踏响黄土路,尘烟扬起,像一条灰蛇蜿蜒北去。
途中经过一座塌陷的桥,桥下河水早已干涸,唯有一块石碑半埋沙中。碑上刻着几个模糊大字:“殉学者七十三人永念”。我让老汉停下,走下来看。拂去泥沙,发现背面竟有新刻的小字:
>“其中六十四人并非死于火灾,而是被注射‘静默剂’后活埋,作为‘群体性恐慌消除实验’对照组。”
我蹲下身,用指甲在泥土上临摹这段话,然后取出一支竹笔蘸血补上一句:
>“他们的名字,不该只剩编号。”
刚写完,身后传来??声。回头一看,三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正躲在树后偷看。见我回头,最小的那个怯生生走出来:“我们……我们在找哥哥。他说他要去京城找清忆司讨说法,一个月前走了就没回来。”
我问:“你哥叫什么名字?”
“林昭。”少年咬着嘴唇,“他是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火灾那天他在整理遗物档案,后来就被抓了。”
我的心猛然一沉。
林昭。那个曾在《小人物志》残卷批注栏里留下“记忆若不能流通,便成了坟墓”的人;那个偷偷复制了十七份原始记录并藏进不同地点的男人。他曾是我寻找真相路上最重要的线索提供者之一,但在三年前的一次突袭中失踪,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可现在,有人看到他进了京城。
“你们怎么知道他去了清忆司?”我问。
“因为他留了信。”少女从怀里掏出一块布巾,展开后露出几行细密针脚绣成的文字:
>“若我不归,请往西岭寻‘讲故事的人’。带上这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