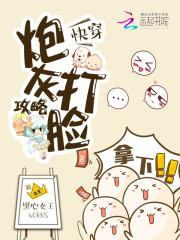笔趣阁>大唐协律郎txt全文免费阅读 > 0541 此计若成流芳千古(第2页)
0541 此计若成流芳千古(第2页)
阎麟之出列奏道:“启奏陛下,臣近日检视边镇奏报,发现朔方监军使李衡任职三年,屡次擅调兵马,且未经兵部备案。更有甚者,其所辖军资账目混乱,疑似挪用军饷。为防患未然,臣建议召其回京述职,彻查其任内诸事。”
此言一出,满殿哗然。萧嵩之猛地站起:“阎公此议太过草率!李衡乃宗室之后,镇守北疆有功,岂能因几句风闻便轻易召回?此举恐寒将士之心!”
阎麟之不慌不忙:“臣所据者,并非风闻,而是实证。请陛下过目。”说着呈上李?提供的卷宗。
玄宗翻阅片刻,眉头渐蹙。他并未立即表态,而是转向一直沉默的另一位宰相张九龄:“曲江先生以为如何?”
张九龄缓步出列,声音清朗:“臣以为,阎公所虑极是。边将久镇一方,易生尾大不掉之势。历代教训,历历在目。今既有疑点,不妨召其回京,一则澄清是非,二则亦可慰其忠诚。若无问题,自当厚加赏赐;若有差池,亦不失朝廷法度。”
玄宗微微颔首,又问高力士:“老高,你说呢?”
高力士躬身答道:“奴婢以为,李衡虽在边疆,然其父李?尚在京师养老,若其子无过,断不会惹祸上门。不如派一亲信大臣前往朔方查访,既显宽仁,又察实情。”
阎麟之当即反驳:“陛下,边将勾结之事,牵涉禁军将领,若派人前往,恐打草惊蛇。不如速召其归,当面对质,方可水落石出。”
殿中一时陷入僵持。玄宗沉吟良久,终是开口:“准阎卿所奏。即日起,敕令下达:命朔方监军使李衡即日卸职,返京述职。沿途不得延误,违者以抗旨论处。”
圣旨一下,萧嵩之脸色煞白,嘴唇微抖,终究未再言语。
退朝之后,张岱随阎麟之走出宫门,忽觉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是许久不见的太子李瑛。他身穿常服,身边仅带两名内侍,神情却异常凝重。
“阎公留步。”太子低声道,“方才殿上之议,可是冲着我来的?”
阎麟之躬身行礼:“殿下何出此言?臣所为者,唯国法耳。”
太子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苦笑:“你们都说要护我,可每一次‘护’,都会让我更危险。昨日有人说我在府中设坛祈福,涉嫌厌胜;今日又要查什么边将……难道就不能让我安生一日?”
阎麟之沉声道:“正因为有人想让您不得安生,臣才不得不动。殿下若愿束手待毙,臣无话可说。但若您还想保住东宫之位,就必须信任我。”
太子默然良久,终是叹了口气:“罢了……我相信你最后一次。可若再有风波,我不再忍了。”
说完,转身离去,背影孤寂而决绝。
回到门下省,阎麟之立即命人封锁消息,严禁李衡召回之事外泄。同时密令御史台派出暗探,监视李?、萧嵩之等人行踪,并加强对宫中宦官往来的稽查。
三日后,朔方快马传来消息:李衡接到诏令后,称病推延,拒不启程。又两日,其麾下一校尉私自离营,携带密信南下,途中被拦截,搜出蜡丸一封,内藏血书:“若主上问及军饷事,宜速决之,勿使我父子俱陷。”
阎麟之看完密报,冷笑不已:“果然心虚至此。”
他当即拟就弹劾奏章,列举李衡七大罪状:擅调边军、私吞军饷、勾结禁军、抗拒诏命、图谋不轨、欺罔圣听、贻误边防。并附上缴获密信原件,请陛下即刻下令缉拿归案。
奏章呈入宫中,当夜便有雷霆之变。
四更时分,三百飞龙骑突袭李?府邸,将其全家软禁。与此同时,宫中传出圣谕:左骁卫大将军李?即日免职,交由大理寺审查;其子李衡以谋逆罪通缉,凡藏匿包庇者,同罪论处。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惠妃连夜求见皇帝,哭诉冤屈,却被挡在甘露门外。她怒极攻心,当场晕厥。而寿王亦被责令闭门思过,不得擅自出入。
五日后,李衡在洛阳附近被捕,押解回京途中试图自杀未遂。审讯之下,供出幕后牵连者数十人,其中包括陈玄礼、两名羽林军将领及三位地方节度使幕僚。高力士闻讯震怒,亲自督审,斩杀叛党七人,流放十余人,禁军系统为之大洗牌。
至此,一场酝酿已久的政变阴谋彻底瓦解。
半月后,玄宗亲临兴庆宫设宴,犒劳有功之臣。席间,他举杯对阎麟之道:“若非卿洞察幽微,运筹帷幄,朕几为奸人所欺。自此以后,门下省事务,尽付卿手,不必事事请旨。”
阎麟之跪拜谢恩,神色谦恭,却掩不住眼中锋芒。
宴罢归途,张岱与阎麟之并肩而行。夜风拂面,星河璀璨。
“相公,”张岱轻声问道,“接下来呢?惠妃虽败,但她仍在宫中,寿王也未被废。这场风波,真的结束了吗?”
阎麟之仰望星空,缓缓道:“风雨总会再来。但我们已立于高地。只要太子稳坐东宫,只要制度仍在运转,只要还有人愿意守住底线,大唐就不会倾覆。”
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张岱:“你可愿继续走下去?”
张岱望着这位亦师亦父的男子,想起这些日子的腥风血雨,想起武氏的泪水、李?的悔悟、太子的孤独,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
“学生愿追随相公,直至最后一刻。”
阎麟之笑了。那是张岱第一次见他笑得如此轻松。
远处,钟鼓楼传来悠扬的夜鼓声。长安城依旧灯火点点,如同不灭的星辰。而在那深宫尽头,一轮新月悄然升起,照亮了无数人的命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