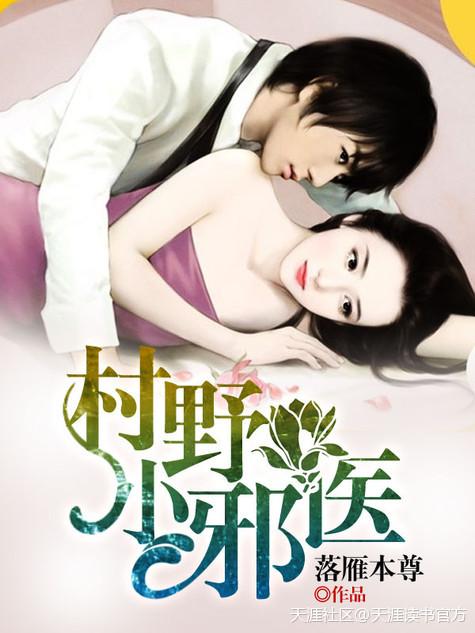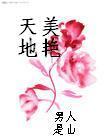笔趣阁>你就写文娱免费阅读 > 第二百八十九章 都在歌里了(第2页)
第二百八十九章 都在歌里了(第2页)
夜半,风起。
她忽然听见远处传来断续的歌声??不是电子合成,也不是广播外放,而是真人吟唱,带着明显的颤音与气息不稳,像是年迈者竭力维持的旋律。她屏息细听,竟是内蒙古长调《孤独的白骆驼》,歌词讲述一只离群的骆驼穿越戈壁寻找族群的故事。
她猛地起身,循声而去。
穿过三道岩脊后,她看到一座半塌的土屋,门前坐着一位裹着羊皮袄的老人,手里抱着一台老旧的磁带录音机,正在播放自己录制的歌声。他脸上布满沟壑,右耳缺失大半,左眼浑浊,但眼神清明。
“你是来找井的吗?”他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有力。
莉娜怔住。“您怎么知道?”
老人笑了笑:“因为我也等了三十年。我是苏老人的学生,叫巴图尔。老师临终前让我守在这里,说‘当风开始写字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接话’。”他指了指头顶,“昨晚,沙粒拼出了你的名字。”
莉娜浑身一震。
她从未对外公布过姓名,甚至连陈砚都只称她为“信使”。
“你怎么认识我?”
巴图尔从怀里掏出一块铜片,上面刻着复杂的螺旋纹路。“这是‘听语印’,老师留给我的唯一信物。它不记录文字,只储存声音的形状。每当有真正纯净的共述者靠近,它就会发热。”
他将铜片递给她。莉娜接过瞬间,指尖传来温热,如同握住一颗跳动的心脏。
她终于相信,这一切不是幻觉。
两人彻夜长谈。巴图尔告诉她,苏老人年轻时曾在青海湖畔做过气象观测员,某夜雷暴过后,他连续七天听见地底传出规律震动,频率恰好与舒曼波吻合。起初以为是仪器故障,直到他尝试对着大地说话,第二天风中竟带回了相似节奏的回应。
“老师说,地球不是死物,它记得所有落在它身上的声音。”巴图尔说,“哭声、笑声、誓言、谎言……全都沉在岩层之间,像树根一样蔓延。只要找到合适的频率,就能唤醒它们。”
他拿出一张泛黄的手绘地图,标注了十三处“声穴”,分布在亚洲腹地的不同地貌中:火山口、盐湖、峡谷、古墓群……每一处都曾发生过大规模集体情感事件??战争、迁徙、祭祀、饥荒。
“你们激活的不只是技术,”他说,“你们唤醒的是土地的记忆。”
翌日清晨,莉娜决定改变计划。她不再单独前往#089,而是邀请巴图尔同行,共同组建“声穴巡礼团”。他们要以月井村为起点,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北线,逐一唤醒这些沉睡的共振点,形成一张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活态声网。
她通过加密频道发布召集令:
>“如果你愿意说出真实的故事,
>如果你愿意安静地听完别人的一生,
>如果你还记得,曾经有人握着你的手说‘我在听’,
>那么,请来敦煌以南八十里的鸣沙山。
>我们将在第七日黄昏,让沙丘替我们唱歌。”
消息发出后第四十八小时,已有来自二十七个国家的三百余人响应。有人徒步穿越边境,有人变卖家产购买设备,有人甚至伪造身份文件只为加入这场无声的起义。
第七日,鸣沙山脚下。
莉娜站在高坡上,望着眼前这支奇异的队伍:穿校服的学生、戴头巾的老妪、拄拐杖的退伍军人、抱着婴儿的母亲、戴着耳坠的程序员……他们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发声装置??陶笛、铜铃、录音笔、老式唱片机,甚至只是自己的喉咙。
巴图尔点燃篝火,将第一块玄武岩安置在预定位置。十二名代表依次上前,讲述自己生命中最不愿遗忘的一句话。